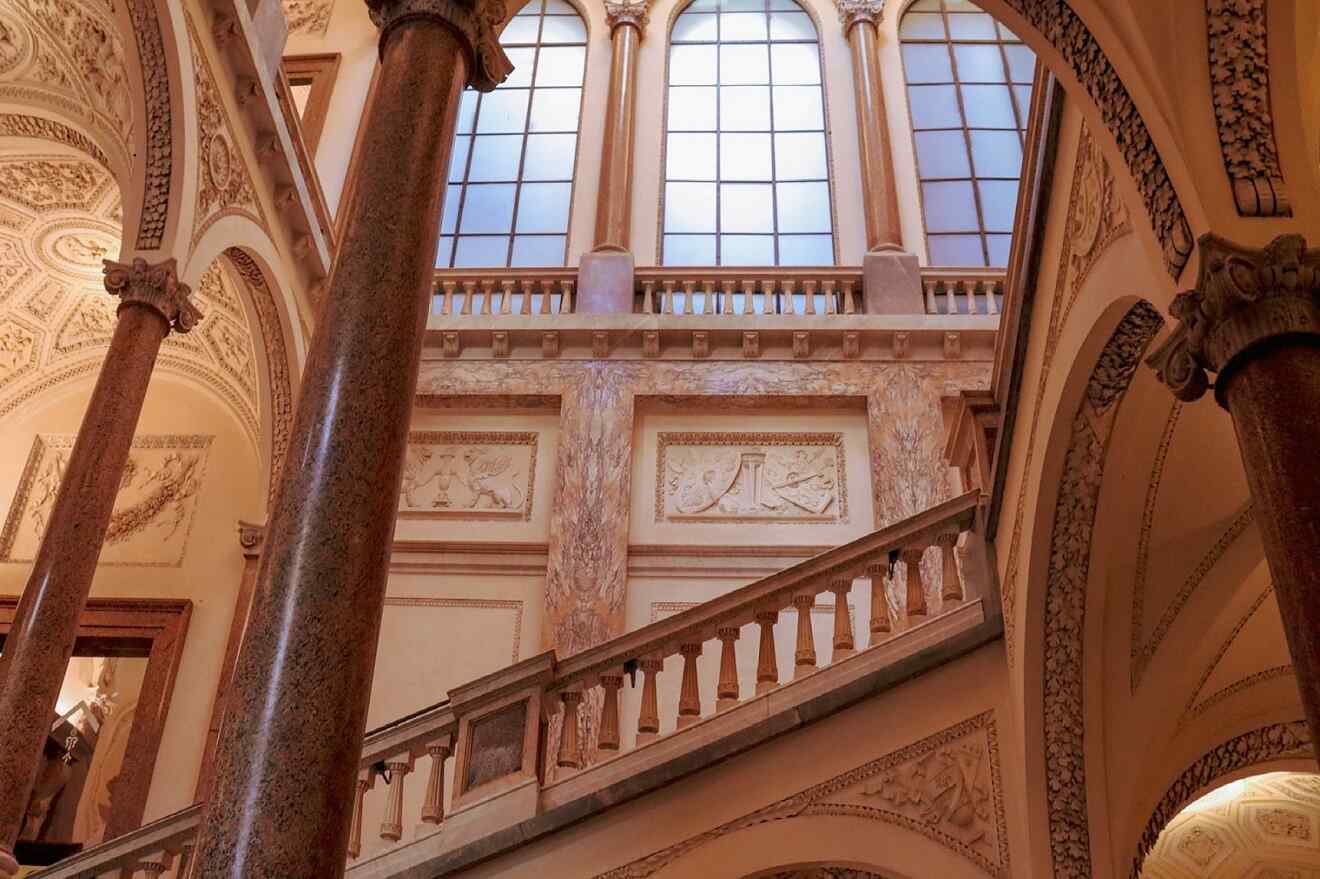
这一阶段以《魔笛》中的帕帕盖诺(Ppgw)为代表。把本质的同偶然的分开,召唤想象中的帕帕盖诺而忘记在歌剧中真正的那个人,自然在这里同样很重要。此处尤其如此,因为剧中的那个人物似乎说着各种各样可疑的胡言乱语。由于这个原因,也许倒是很有兴趣把整个剧本查一遍,发现它被看作是歌剧题材的主题,完全不能达到它的目的。我们还有机会从一个新的侧面来阐明。因为我们注意到如何努力把它置于一个更深层次的伦理观中,这种伦理观以这种方式尝试各种各样的更有意义的辩证练习,是一种超出音乐范畴的冒险,因此甚至一首莫扎特的作品也不可能引起它更浓厚的兴趣。这首歌剧最后趋于非音乐了,因此尽管有个别完美的协奏曲部分,也有个别深深打动人心的叙述,但绝对称不上是经典的歌剧。此外,这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小小的研究的对象。我们只需研究一下帕帕盖诺即可。这对我们大为有利,如果只为这个缘故,我们似乎不必试图去解释帕帕盖诺同塔米诺的关系的重要性。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故事梗概而言,显得如此之意味深长、体贴入微,以至于其纯粹考虑之周全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欲望苏醒了,如同一贯的情况,我们只在苏醒的那一瞬间意识到自己做过梦,这里也是如此,梦已经结束了。随着欲望苏醒的这种冲动、这种战抖,将欲望和其对象分开了,赋予欲望一个对象。这是必须牢记在心的一个辩证的限制——只有当欲望的对象存在时,欲望才存在,也只有当欲望存在时,其对象才存在;欲望和其对象是一对李生兄弟,谁也不比谁早降生片刻。然而,尽管它们完全在同一时刻降生,在出生时间中间没有间隔,跟其他孪生一一种,但它们这样来到人世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连体降生,相反,在于它们是彼此分离的。但这种感官上的运动、这种震撼,瞬间将欲望跟它的对象无限地分离开来;但因运动的原则是似乎是瞬间的分离,所以它又显示出想把分离中两者联结起来的愿望。这种分离的结果是欲望不再潜伏于它内在实质性的休眠中,结果其对象也不再受实质性的限制了,而是把自己分散为多个层面。
正如植物的生命依赖于土壤,所以第一阶段也束缚在实质性的渴望之中。欲望苏醒了。其对象却逃离了,它将自己从多个层面显示出来;渴望摆脱了土壤并开始漫游;花儿被插上了翅膀,飘忽不定、不知疲惫地到处飞掠而过。欲望转向它的对象,内心亦被打动,心儿欢快地跳动,那对象迅速地不断消失又重现;但在每一次消失之前都有片刻的快乐,瞬间的接触,短暂却甜蜜,如同萤火虫微弱的闪光一样转瞬即逝,如同蝴蝶的飞掠一样飘忽不定;如同那些丝毫没有害处的无数的亲吻,快乐如此短暂,以至于就像它取自这个对象身上,而它原本是属于下一个对象的。一种深层的欲望只是在瞬间被怀疑,但这种怀疑已被遗忘了。在帕帕盖诺身上,欲望的对象是发现。对发现的渴求在它体内跳动,是它的生气所在。它并没有在这种寻求中找到确切的对象,但它在探寻想发现的对象中发现了多样性。
欲望因此苏醒了,但它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欲望。如果你还记得欲望存在于三个阶段中,那么你可以在第一个阶段中欲望被称为“梦想”,第二个阶段称为“寻求”,第三个阶段称为“渴望”。“寻求”的欲望还不是“渴望”的欲望;它仅仅在寻求哪些它能寻求,但它并没有渴望得到。因此下面的话将是对其最佳的描述:它在发现。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把帕帕盖诺同唐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后者的游历世界之旅不仅仅是次发现之旅;他不仅享受发现之旅中的各种快乐,而且是一名志在征服的骑士(我来到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发现和胜利在这儿是等同的;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会说他在征服中忘记了发现,或发现在他的身后,因而他把它留给他的仆人兼秘书莱波雷诺,同我想象帕帕盖诺保存书本相比,他完全在另一中意义上保存名单。帕帕盖诺负责挑选,唐璜专管享乐,莱波雷诺重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