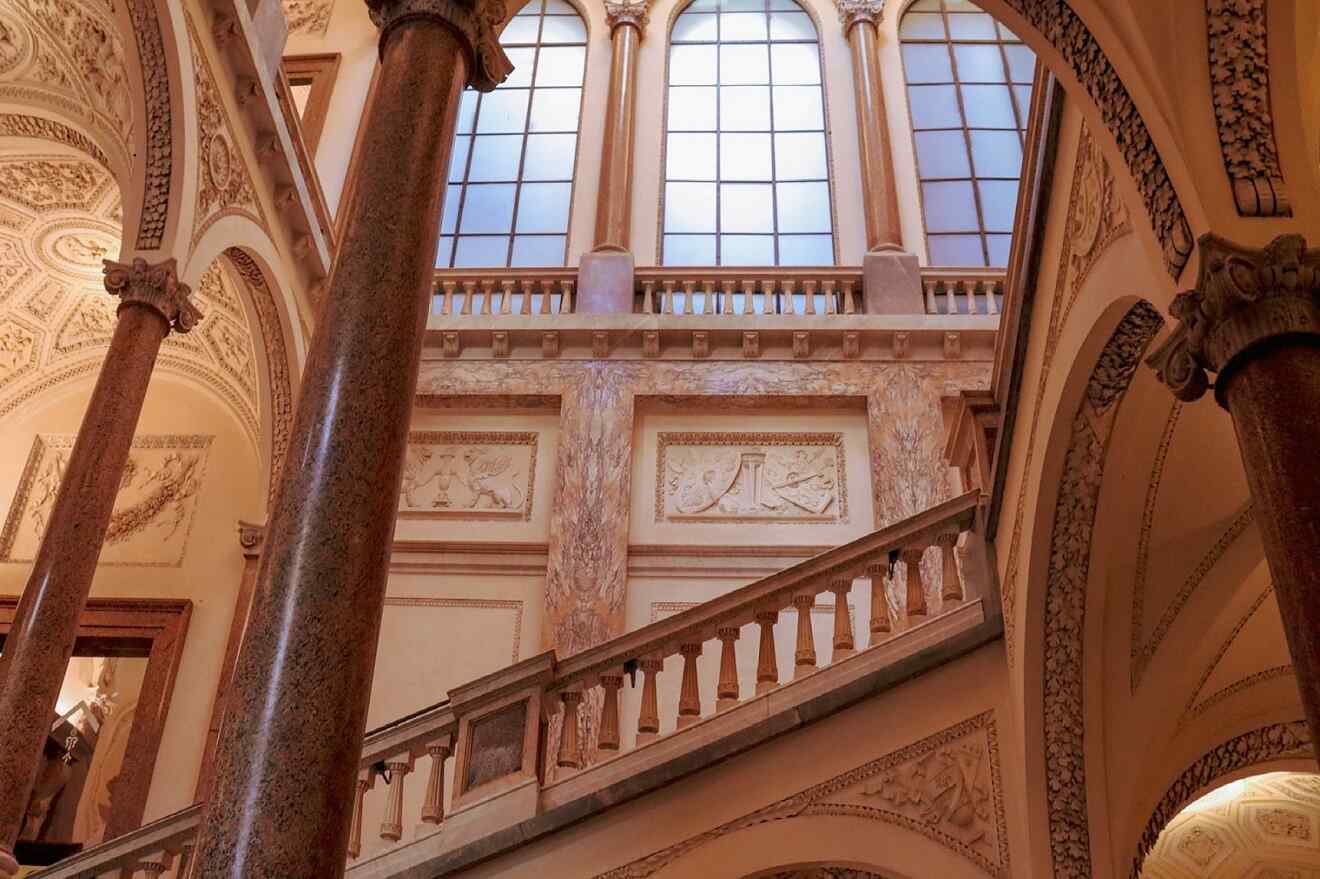
全文转自:男中音歌唱家田玉斌与栾峰谈歌唱
我与栾峰很早就认识,那还是他在总政歌舞团工作的时候。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作为年轻的男低音歌唱家,在声乐圈儿里很活跃,经常出现在各种音乐会中,记得我们还同台参加过一些音乐会的演出,自他去了意大利以后就断了联系。近几年从国内媒体的报导中得知他回国了,并被我国很多音乐学院聘为声乐客座教授。今年六月我们共同参加了“哈尔滨之夏―第八届全国声乐比赛” 的评委工作,我利用此机会完成了这本书的最后一次访谈。
2008年6月26日在我们评委的住地哈尔滨国际饭店和回北京的飞机上,分两次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田:咱们先从你在总政歌舞团的时候说起好吗?
栾:可以,我十七岁那年考取了总政歌舞团,进团后随男低音歌唱家杨比德先生学习声乐。,跟刚刚从意大利学习归来的男中音歌唱家黎信昌老师学习。1987年幸运的被选中参加“香港国际音乐节”的演出,当时与我同去的还有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我们去排演的是莫扎特的歌剧《魔笛》,迪里拜尔饰演剧中的夜后,我饰演剧中的太阳神-萨拉斯特罗。这也是我艺术生涯中演出的第一部歌剧,正是由于这次机会,使我与意大利结下了不解之缘。
田:演出是用德语唱的吗?
栾:面试的时候唱得是德语。但因为是在香港演出,所以又要求我们用英语演唱。这部歌剧总共要演出六场,主要角色有两组演员,一组是外国人,一组是我们。几天排练过后,指挥和导演决定,太阳神-萨拉斯特罗六场全部由我一人担纲。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之后还在香港演艺学院又为我举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但带给我最大的惊喜是意大利驻香港的总领事麦凯蒂先生也来观看了我们的演出。演出后他找到我,问我是不是香港人?告我意大利政府每年给香港地区几个政府奖学金名额,用于资助那些在音乐、美术等领域的艺术人才去意大利进修深造。他决定把那年去意大利的政府奖学金名额给我,并希望我能尽快去意大利学习语言和意大利的歌剧。当时我心里高兴得就像见到了上帝一样,我想对每一位有追求的声乐学者来说意大利这一国度就意味着心中的天堂。
田: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
栾:是呀,小的时候我妈妈常跟我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参加工作后,让我更深刻的认识到,机会是给有备而来者的礼物。香港演出结束后我马上回到北京,很快便办好了去意大利学习的手续。,能在总政歌舞团这样的国家级团体工作是很幸运的,要离开这样的工作单位也是需要点魄力的。
去意大利的前一天晚上,我最后一夜躺在总政歌舞团“光棍儿”宿舍的单人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我盯住床头一张贴了多年的世界风光挂历,这张挂历上的风景正是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看过它多少遍了,想想在中国这么多学习声乐的大军中,我能有幸去意大利这一歌剧的故乡,亲眼目睹,亲耳聆听意大利人怎样演唱歌剧,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呢?其实我一点经济基础也没有,也不知道那份奖学金在意大利能是个什么活法,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田:讲讲你在意大利学习的情况吧?
栾:我去的是意大利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那里的声乐教育仍是很传统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学习声乐的东方人比西方人多,东方人普遍有点心急,尤其是日本人他们有经济实力,上午上一课、下午上一课、晚上还上(当然是找不同的声乐老师)。以为这样“ 提速”一天三课就能唱得和意大利人一样了。当时我是没钱,那种想速成的心态和他们也差不了多少。但意大利的声乐老师们从来不急,他们大多是托斯卡尼尼那个年代有成就的歌唱家,非常明白急于求成是没有用的(我说的是那些负责任的声乐大师们)。有一次在课堂上,我的老师“吼”了我一句;急什么!米兰大教堂盖了几百年还没盖完呢?
学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开始了解了什么是意大利的传统声乐观念,比如不同的声种类型都该选唱些什么,什么年龄段应该先唱哪些作品。我们所选唱的一些作品几乎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或对某位歌唱家的崇拜来选定的,很少考虑是否适合自己的声种类型。在演唱过程中,甚至在音色上都去效仿心中崇拜的偶像。我的意大利老师就曾问过我最喜欢哪位男低音歌唱家,我说保加利亚的尼可拉伊?恰乌洛夫,他说难怪你唱得那么像他!当时听了这话还美滋滋的,以为是在夸我呢。他建议我先放放这些唱得有些偏重的曲目,改唱莫扎特的一些声乐作品,对于他的建议当时我心中很是有点抵触情绪!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也在练习莫扎特的作品,但心里却依然割舍不下威尔弟的那些咏叹调……
田:带着这种心态,你是怎么学下去的?
栾:通过参加国际声乐比赛和一些演出实践,开始逐渐醒悟到导师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我参加过几个国际声乐比赛,也拿过几次奖,但始终没获过第一名。在我参加过的比赛中,亚洲的男低音选手没有遇到在我前面的。但是有两个男低音教育了我,他们分别是意大利人和苏联人,这两个男低音令我深省,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首先是他们的身高,均在一米九左右,他们用声音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威尔第类型的声音。
现在这两位歌唱家都活跃在世界的歌剧舞台上,意大利的那位男低音曾在张艺谋导演的歌剧《图兰朵》中饰演过帖木尔。这位男低音年龄比我还小一点儿,可是他的声音威力至少比我大一倍,苏联的那个男低音年龄比我大几岁,声音类型和意大利的男低音非常相像,虽然他们俩人的演唱方法有所不同,但在他们的声音里没有做作的音色,也绝非撑出来的音量和威力。这让我想起了导师的话,唱莫扎特你是个大男低音,唱威尔第你是小男低音。当时我不完全懂这话的深刻含义。这正是他们传统声乐观念的一部分,有一天能把这一观念消化了、理解了,也就进步了。
田: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些学声乐的人观念是很难改变的
栾:记得有一次在维也纳面试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医生-巴尔托洛,经纪人听完说:“你演唱巴尔托罗,让我们去哪里找费加罗呀?你的声音应该唱费加罗才对”虽然是句笑谈,却又一次证明了我的声乐导师最初给我的建议是正确的。这位老师离开我已有好几年了,直到今天我仍在回味着他的一些英明教诲,想到当时自己既无知又固执真是惭愧万分。如今教过我的三位意大利老师都已去世多年,他们是男低音歌唱家罗西? 雷美尼,男中音歌唱家吉诺?贝基和蒋皮艾罗?马拉斯必纳教授。我非常庆幸自己赶上了跟他们学习的那个年代,在那一代歌唱家身上才能真正学到什么是传统的意大利声乐观念,什么是声音美的尺度,什么叫美声唱法。
田:意大利老师在声音技术上是怎样训练的?
栾:意大利的声乐课也没什么特别的,先练声、后唱作品。然而他们的耳朵对声音的审美与我们想象中的声音效果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并没有科研出什么新招,依旧是按部就班的训练,做的每条发声练习也并不复杂。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的声音轻松灵活了,尤其是在换声区的地方简单容易了。我想,这一神奇的变化统统跟意大利老师的耳朵对声音敏感的判断,和要求发声的精准尺度有关系。说到这里有句话我必须要说,今天意大利的老师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有了不小的差距……
田:你能否把换声区怎么变的容易了说的再具体点吗?
栾:当然可以,也许我换个说法更容易阐述明白。首先要把握好中声区演唱的尺度,往上下唱自然就容易了。我们往往在自然声区(也就是中声区)唱的太大太满,因此到高声区的时候必然会成倍的放大,这种状态到了一定的高度上声音就会显现出敞着喊的感觉,这时有不少人企图用加点O或U来遮掩一下,使声音似乎变暗了,这并没有真正解决换声区的问题。由于打开得尺度不准确,即便是用加了O或U的感觉往上唱依然带着一种附加的力量。说的再直白点,用别的元音去遮掩一下敞着喊的感觉,并不能解决上高音的技术,意大利人上高音的技术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要做到声音在换声区正确的转换,首先要认真打磨自己的中声区,正确认识自己的声种类型和音色,只有把中声区唱得轻松流畅,尺度准确,在换声区的过度上自然也就容易了。他们好像不太刻意去讲,到了换声点应该怎样去做,也许因人而异吧。在咬字的同时一定要提前就贴住位置,或者说翻上去。这一细微的感觉其实可以从较低的声区就能体会到。再详细的技术动作纸上谈兵是说不清楚的。一定是要因人而异,这一点我个人的体会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必须要耐得住慢慢炖!
田:是的,成就一位歌唱家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除了个人的努力外,你怎么看老师的指导作用?
栾:学习声乐起步时,老师的指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帮助你认识自己的声种类型,确定声部,用正确的训练手段使你的歌唱肌肉,呼吸状态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我认为音乐学院四年或五年的教育体制是非常短暂的,在这四年或五年的学习训练中,能树立起正确的声音观念,不走弯路,已是万幸了。想从事声乐歌剧职业的人必须要具备三点基本的要素;一是爹妈给你的生理条件,二是要有很好的悟性,三是必须从骨子里热爱这一行,也就是嗓子加脑子再加用功!不具备这三点要素的人是坚持不到最后的,因为学习声乐的过程确实是一个艰苦的里程!
田:咱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话题说,在声乐观念上除了要分清声种类型外,还有哪些更重要的技术?
栾: 有个关键的技术问题就是语言,这是所有亚洲声乐学者难以逾越的一道门槛。有多少好嗓子被拦在了这道门槛之外。这几年我去过很多音乐学院讲学,发现这一问题相当严重,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演唱时清浊辅音不分,双辅音不会发,双元音、三元音含糊不清,更不求语气重音和意思上的甚解,有多少漂亮的声音,演唱只停留在这样一个尴尬的段位上,真是太可惜了!各大音乐学院对这一问题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了。那些唱歌喜欢瞎使劲的人,一旦弄懂他们在唱什么,声音只会更加漂亮。意大利歌唱家发出的漂亮声音,技术是往字上着力,我们由于不懂这门语言,演唱时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声上,想唱出意大利人那种有穿透力的声音,结果力量全用到了嗓子上,这是发声技术上最大的误区和不同。
田:说外国人不讲究咬字,绝对不是这样的。
栾:当然不是,意大利人非常讲究咬字,只是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亚洲的声乐学者是另外一门学问,更可以说是一门演唱的技术秘籍。您发现没有,来我国讲学的大师专家们上课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弄语言上?
意大利人的教学语言非常直白简单,最常用的有两句话,一是放在呼吸上, 二是打开。当然也会纠正你的吐字发音,而我的感觉是,吐字发音的准确更为重要,会帮助你更好的体会在呼吸上打开的尺度。由于我们不懂演唱的语言,不敢把歌词往极致里咬,字总是含在嘴里没有真正着上力,这样唱的声音位置也是模糊的。意大利人的字实际上发的特别“白”如果认真听听帕瓦罗蒂或更早期的歌唱家们,如男高音;卡鲁索、吉利、斯基帕等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咬字发音才是美声唱法最关键的技术。在这里我不得已用了个“白”'字来形容这一技术,实在是因为说“靠前”很多人已经听不懂了。“白”强调的是在演唱时咬字的一种技术状态,不是让你出大白声,(他用两种不同的咬字方法示范唱了《我的太阳》中的“Ma natu sole”一句,让我感受了一下他强调的咬字“白”与不“白”的区别)
田:这可能对于多数学习声乐的人来说是难以做到的!
栾:想演唱明白必须要弄懂字与声的关系。意大利人经常自信的说:正确的方法只有一个!我非常同意他们的这个说法。在跟艺术指导或指挥做音乐作业的时候,我常有这种感觉,如果弄懂了每个乐句的意思,歌唱的能力似乎解放了一半还多。有时我不自信的问:“就用这么大劲儿唱吗?”“ 对!用这么大劲儿就够了,已经很好了。”然而我的感觉是连一半儿的劲儿都还没使上,他们说够了。这不能不发人深省,我们认为“用”上时,是使了多大的“劲 ”呀?
田:你的这个感受别人还真的没有涉及到,请谈谈。
栾:我们在演唱时总是怕自己没有用上,结果人家说你用过了。在意大利我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付耳朵,它极其敏感的帮我把握着声音的审美尺度。搞声乐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当然也包括我在内,都怕自己的声音小,听上去不过瘾。也不管自己是什么条件,什么声种类型,就情不自禁的投入到追求“大”的误区里去了。凡是唱的大过了自身条件的声音,一定是位置偏低,声音摇晃,撒气漏风,甚至大到已经失去了咬字的功能。我经常听到有些年轻人拼到要上高音时,肌肉再也没有张力了,只好张着大嘴也不咬字了,一啊了之。这种情况大都发生在嗓音条件超好的人身上,也许他们听到太多带有“戏剧性”字眼儿的赞美了吧。
田:这的确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你谈的很深刻。
下面换个话题
那天咱们聊天儿的时候听你讲,在意大利找过吉诺·贝基先生。
栾:准确的说是在一次国际声乐比赛中的巧遇。那是我参加的最后一个国际声乐比赛——意大利“ 吉里”国际声乐比赛。这次比赛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获得了第一名。贝基先生是这个比赛的评委会主席,当时我并不知道,因为台上特别亮,在上面演唱根本也没精力去注意评委是谁。直到比赛结束评委们上台颁奖时,我才惊喜的认出了是吉诺?贝基先生。多年不见他老了许多,头发已全白了。他给我颁的奖。并对我说:“ 我非常喜欢你的声音,当时好像还问过我在中国跟他上过课的人唱的怎么样了?”他给我留了家里的电话号码,让我有时间去找他,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个幸运的号码。上帝对我真是开恩,刚结束在威尔第音乐学院的进修,就又把我带到了意大利美声唱法的“真神”面前。
田:你去找过贝基先生吗?
栾:当然去过!后来就一直跟贝基先生学习,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在意大利授予他终身成就奖时,他还约我参加了那场颁奖音乐会。
贝基先生晚年住在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半山的别墅里,那时我每星期从米兰跑一趟佛罗伦萨,去贝基先生家上课。,家具看上去有点像歌剧里的道具,墙上挂着一面中国国旗,很显眼,上面有很多在北京跟他上过课学生们的签名,他从中国回意大利后逢人便说——中国的好嗓子遍地都是,一筐一筐的。
贝基先生是我的第三个意大利老师,也是最后一个。从他这里我明白了很多很多,更可以说是明白了美声唱法的真谛。跟这样的大师学习,你自己也要在一定的段位上,否则依然是很朦胧,像大炮打蚊子。有些是他说明白的,有些是他通过示范演示明白的。其实他的很多技术观念在我国讲学时都曾说过,只是那时我们还理解不了。简单的说如果我根本不懂意大利语,依然难以明白他要求的字与声的关系,可能也听不懂他的示范精湛在哪里。他唱得很薄,很靠前,绝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重。如果你能听懂意大利语,就会发现他的咬字有多么清楚,发音有多么靠前,或者说有多么“白”。这是句有技术含量的话,够段位的人才能听懂。
田:我从另外几位外面回来的人那里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你说贝基先生在呼吸上给你很大帮助,能不能谈谈?
栾:当然可以,他说气吸进去的时候应该是向两边扩张,而不是肚子鼓起来。你听说过吗?
田:我的印象不是这样的。
栾:我做给你看(他站起身来示范),在我们的印象中气吸进去后腹部应该是出来的,但完全不是。他要求气吸进去往两边儿走,小腹是收进去的。他让我用手掐住他腰部的两边儿,吸气时横膈膜的周围向外扩张,与此同时小腹自然收回。
田:这样是对的。
栾:这种呼吸状态是不一样的,演唱时很容易用上。但不要机械地去做,要非常自然的去体会,下意识的滞在那里(他示范演唱时用气的感觉)。跟贝基先生,我学会了根据乐句来设计自己的呼吸,不能什么乐句都用一种呼吸方法。呼吸有从容的,有急促的,也有偷气,要在音乐性里完成。把呼吸纳入音乐表现的一部分,连换气都在情绪里,在戏里,在语气里,气并不是吸得越多越满越好。
田:除了呼吸之外,贝基先生在打开喉咙方面是怎样要求的?意大利在这方面都有些什么说法?
栾:说到打开,几乎所有的声乐老师,都会强调这一技术。但为什么意大利人的打开和我们打开后的效果不一样呢?因为意大利人的打开是有尺度的。而我们是盲目的,或者说是不知深浅的无度的打开。这种无知无度的打开害了很多人!
田:请你讲讲意大利人打开的度是什么?
栾:意大利人打开尺度的依据是语言,还有声区。我们都知道意大利语的五个元音有宽有窄,声区有高有低,在不同的声区上咬不同的字,打开的尺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意大利人打开尺度的依据。他们很少莫名其妙的狂张大嘴,今天声乐演唱水平不断的退步,就是跟这种无度的打开有很大关系!今天的意大利人也无法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不知是人们对声音的审美发生了变化,还是耳朵出了问题?
声乐老师们强调打开,并没有错,但错在没教会学生在自己的条件上应开多大为适度!每个人的生理结构不一样,打开的尺度自然是不一样的。这里没有可以用文字来表述的定律;有的人开这么大声音依然是结实的,你也开这么大,声音没准就是糠的,没有密度的,撒气漏风的。要找到自己在不同声区上,发不同元音时准确的打开尺度,才能越唱越轻松,越唱越容易,越唱越明白。
田:你所说的靠前是指面罩吗?
栾:是的,面罩这个术语是准确的。怎么才能让声音挂在面罩这儿呢?这跟咬字的习惯,咬字位置的前后有关系,(他示范两种咬字位置不同的区别),字咬的靠后或太松,肯定难以体会到声音贴在面罩上的感觉。盲目的放大演唱,无非是想让声音更宽大、浓厚。然而在忽略了这一技术观念时,只想唱得更像某个声部,那很可能是假像,不是真像。技术观念对了该是什么声就是什么声。不要怕往前唱是不是不像男低音或男中音了,有些人在上高音的技术没有真正解决前就误认为自己是中低音,便开始撑着喉咙找音色,那是种人造音色,很难听。要唱爹妈给你的音色,或者说上帝给你的音色。意大利的男低音听上去似乎没有东欧的男低音那么浓厚,但是非常结实。
田:只有像你这样长期在那里工作生活的人才能做出这样明确细腻的比较。
栾:所以我敢说东欧虽然出了很多歌唱家,名气也不小,但他们不是意大利唱法,声音里做作的成分太多。
田:你喜欢男低音-夏里亚宾吗?
栾:非常喜欢!我认为他是意大利的唱法,声音结实不重,轻巧灵活,音色很像意大利男低音恩佐平扎。
田:他的声音跟卡鲁索和贝基的感觉很像。
栾:是的!每个国家都有明白人,真正弄明白的人,一听就知道夏里亚宾不是俄罗斯学派的。他实在是太特殊了,所以他的名字可以流芳百世。
田:俄罗斯的男中、低音多少都有点儿做作的成分。
栾:是的,意大利人到俄罗斯去讲学,发现他们的男低音到了小字一组的d和e还都敞着唱。这样唱不科学,而且很危险!
田:我特别高兴你对夏里亚宾的共识。你讲的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要求学习声乐的人,要根据自己的声种类型去自然地歌唱,而不要去做声音。
栾:一点儿都不能做!不管你喜欢的偶像是谁,或喜欢哪位作曲家的作品,一定要坚持唱自己。我特别喜欢男高音,但那不是我的声部,我喜欢威尔第的歌剧,但他的作品有些适合我唱,有些不适合我唱。作为一个职业声乐演员应该知道取舍什么。而不能因为竞争激烈,就什么都揽过来唱,那样玩儿很快就完蛋了。为什么那些歌唱大师可以一直唱到六七十岁?因为他们知道遵守传统的声乐观念。难道帕瓦罗第真的不能唱《奥赛罗》不能唱《阿伊达》吗?他在斯卡拉不是唱过吗,还出过DVD碟。但他很少玩儿这些剧目,只玩儿他的抒情男高音剧目。很多唱莫扎特和罗西尼的人,觉得自己也有能力驾驭威尔第和普契尼,就跨越出了自己的领域,关键是要明白怎么能再撤出来,如果只会跨进不会撤出就离死不远了。这就是意大利传统的声乐观念。我经常拿举重这个项目举例子,重量级和轻量级的冠军都是世界冠军,不要把眼睛只盯在重量级上。
田:你这个比喻很形象。你在意大利近二十年了。谈谈现在的歌唱家,与老一辈的歌唱家有什么不同?
栾:最明显的不同就是,老一辈的歌唱家可以辉煌几十年,现在的歌唱家只能辉煌几年。这说明声乐艺术并没有进步,而是在退步。帕瓦洛第去世后很多搞声乐的人都那么沉痛,他的去世似乎给美声唱法画上了句号!他是最后一个被称之为有意大利美声血统的声音,其它的声音已经不具备这种血统了!我庆幸上帝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在意大利生活了近二十年,我的耳朵早已入了意大利国籍。
田:这二十年,你肯定比别人了解得更多。
栾:是的,这些年我存了很多意大利早年间的影像资料,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在中国我的美声音像资料是比较全的,也许有点儿吹牛了。在意大利有一个时期每天夜里播放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歌剧电影和录像,都是黑白的,主演全是莫纳科、苔巴尔蒂、科莱里、巴斯蒂阿尼尼、贝基、戈比、斯苔芳诺等,都是他们三四十岁,正当年时演唱的歌剧实况,有些资料还要早些。如:男低音罗西?雷梅尼年轻时演唱《费加罗的婚礼》的实况录像,这种资料就非常珍贵。
田:罗西·雷梅尼夫妇曾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过中国,在北京做过讲学活动。
栾:罗西·雷梅尼是世界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他年轻时可以非常轻巧地演唱《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费加罗,这很说明问题,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从莫扎特、贝利尼、罗西尼最后唱到威尔弟的。而我们今天刚刚起步就直奔威尔弟的《唐·卡洛》《游吟武士》等剧目,只能说明我们无知。我现在教学时必须让学生醒悟到,二十岁你该唱些什么,三十岁你该唱些什么。而且要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唱出能驾驭住的速度、力度。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些基础功课都是培养你肌肉良性记忆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让你一开始就唱肌肉容易使劲的那些作品。我觉得声乐教学只能是在一对一的教学中发现问题,而不是泛泛地谈一些理论观念,中国声乐界自创的理论太多了!
田:在声乐教学上真正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并不多,要改变这种局面,只靠一对一的教学方式是很难的。
栾:也许搞讲座和论坛更有实际意义?大家在谈论中就像咱们这样,然后把它整理出来,这比自己去归纳写书要好得多,成了文章之后就没那么精彩了。
田:这正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觉得这样可以把问题探讨得深刻一些。(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吧,下午和晚上还有工作,回头找时间再谈。
(注:以下的谈话在是比赛结束后,7月2日我们在回北京隆隆作响的飞机上进行的)
栾:上次咱们最后谈的是什么话题?
田:上次谈得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应根据自己的声音条件去选择作品,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想唱啥唱啥。
栾: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作为评委在这次“第八届全国声乐比赛”中,看到有些选手第一轮唱得还不错,使我眼前一亮,语言也还说过得去,如果作品选得再合适些,你不会认为他(她)的声音有什么问题。但到决赛时,有些选手的曲目就不对了,他们以为靠作品的分量也能取胜,如果你驾驭不好,不是也暴露其它的问题吗?比如有位女高音决赛时选唱的是威尔第的歌剧《命运之力》中的咏叹调–Pace mio dio,这明显不是她的曲目。比如最后的一句Maledizione,是被诅咒的意思,怎么能这样唱呢?(他示范抒情和戏剧在演唱这一句上的区别)不是嗓门大点儿就一定是戏剧女高音。我们在较细腻的声音种类上划分的太笼统,以为声音偏大些就是戏剧女高音。我听到不少这种类型的漂亮嗓音已经救不活了,真是太可惜了!
田:在这次比赛中的确有许多选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栾:这个问题要两说着。一是现在的声乐教师们越来越年轻,他们掌握的曲目量有限,还不会判断声种类型、声部的定位,那是不行的,会误人子弟的;二是学生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一味地去模仿自己崇拜的偶像,跟着CD乱吼,以为靠模仿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声音。
意大利男高音莫纳科、斯苔芳诺曾在中国声乐界影响很大,大家都想有一天能唱出他们那种声音,但怎么可能呢?如果歌唱家是能够复制的,意大利早就复制出无数个卡鲁索、吉里、莫纳科了;还用等我们去复制吗?吉利、莫纳科、帕瓦罗蒂就一个。人家都在唱自己,而我们在唱人家,他们声音中那种戏剧性的密度、威力、很大一部分是生来具有的,条件是爹妈给的,技术是后天练的。
田:在人们的概念中似乎声音大就是戏剧性男高音或女高音,声音小就是抒情性的,很少从声音的密度上去分辨声音的类型。
栾:声音的密度也可以说是声音的质量,密度越高越结实,穿透力也就越强,也越能彰显出戏剧性的魅力。
田:我理解应该是紫檀和一般木头的那种质量差别吧!
栾:对!你这个例子很贴切。就像紫檀,虽然两种都是木头,但质量完全不同,一小块紫檀很重,就是因为它密度高。声音恰恰是,开的越大密度越小。
田:这次比赛还是涌现出一些优秀的选手,但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声乐教学中的一些问题,你怎么看?
栾:的确有些选手的实力不错,但语言、音乐上还很欠缺,参加比赛不能靠撞大运。记得我第一次跟意大利的老师说参赛的事儿,他不让我去。说没把握拿第一就不要轻易出击。那次我没听他的话偷偷去了,结果只拿了个第三名。后来又参加过几次比赛,都是榜上有名,均未拿到过第一。这说明没炖到那个火候真是不行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再参赛了。但并没放弃过要拿第一的梦想,结果在我的最后一次比赛上,终于收获了我唯一的一个国际声乐比赛的第一名。
我想说的是;通过这次担任评委,发现国内有些选手的心态很急,连他自己都知道没什么把握,却盲目的自信,误打误撞,这种心态非常不好!比赛本应是展示自己,建立自信的一个机会。没有把握就盲目的出击,只会屡战屡败,这样会摧毁你在舞台上的自信,甚至会导致你放弃这一事业。
田:除了这些问题外,你是否觉得我们的音色,尤其是女声的音色与欧洲有什么不同?
栾:有很大不同,欧洲人把字唱的很清楚,打开的技术尺度也比较准确,还有更重要的是,她们唱的是假声,因此唱出的音色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不少人还在大真声上唱,语言也不准,再追求大音量,音色怎么会漂亮呢?我有种感觉非常明显,现在人们的审美是以追求“大”为美,好听不好听,音色美不美似乎不重要。我在保利剧院就听到过这样的赞美:满台就你的声音最“大”。多可怕呀的赞美和误导呀!
“大”可以说是声乐学科里百无一利,第一有害的字眼儿,它就像一颗癌细胞,引发起诸多的问题。位置低、音不准、声乱晃、不流畅等等,统统是因为这颗癌细胞的原因。
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自己认为是大号的、戏剧性的声音,在演唱时已经撑到了尽头,吃力到无法正常咬字、无法控制声音的平稳、为什么就没人提醒他们,你已经“大”到不是你自己了,音色脏了!如果我们的白衬衣上掉上了一点咖啡或菜汁什么的,你会觉得恶心,会马上去处理一下,为什么音色脏了就不觉得恶心呢?
田:你说的我完全赞成。下面要问的是关于意大利的语言,我们在学意大利语时强调五个母音有七种发音,其中E和O两个母音有开口音和闭口音两种发音。
栾:一定是专门教语言的老师这样讲的,这两个元音确有开口和闭口之分,说的时候区别相对明显些。但在唱的时候我不曾记得太强调过这两个元音的发音。(他喜欢用元音-母音)因为学会说这门儿语言之后,开口和闭口发音就变成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了,另外也要看它出现在什么字上。总之在演唱中A E I O U五个元音的纯正更为重要。我发现教语言跟教声乐的老师还是有些区别的,教声乐的老师对演唱中的轻浊辅音不分是不能容忍的,而教语言的老师好像就没那么严重了,因为说话是没有休止和间歇的,歌唱则不同,经常是一个单词因为节奏的缘故会分成两到三部分,如发音不清楚,很可能会出现另一个意思。不会发轻浊辅音、双辅音、双元音、三元音,唱出来总感觉像有点外地口音。跟唱法结合得再密切点说,如果字咬得含糊,声音的着力点就不明确,音色和声音肯定不会漂亮。(他示范唱“我怀着满腔热情”中的第一句)
田:由于我们不懂意大利语,只限于会拼读,所以语言上的问题要想得到彻底改观很难。意大利关于换声区的问题都有些什么说法?
栾: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意大利美声唱法的强项。发声方法正确,过换声区几乎感觉不到有任何痕迹,转换得非常自然。谁都知道人的高、中、低声区,的确存在声区转换的问题,但是意大利老师不像我们这样教;到哪个音了该关闭了!更不是靠加点儿O或U什么的去遮掩一下。他们没有让你刻意地去做什么动作,不管你唱什么元音都得转换过去,他们常用的一个技术词叫—PASSAGGIO,是通过和的意思。 PASSAGGIO做得好就可以顺利通过,前面我曾讲过要打磨中声区的问题,把中声区(自然声区)唱大了,必会出现明显过不去的坎儿,再想顺利的通过 PASSAGGIO就困难了。就像一辆超载的货车,货已经装的超出了规定的高度和宽度,前面的通道自然就过不去了。
田:在解决换声问题上他们有什么具体手段吗?
栾:精湛的意大利方法是,还没到换声点就在提前两三个音那儿准备好了,好的歌唱家很早就可以让声音转换到面罩上去,其实让声音的位置越早贴在面罩上越好!如能掌握好这一技术观念,你根本就不会感觉到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说起来一点儿都不神秘,是我们把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了,人家没有那么多的理论学说,我们的理论太多却又指导不了实践。
田:咱们前面谈的都是技术问题,我觉得除了技术之外,目前学习声乐的人,音乐表现力也很是欠缺,如有位选手演唱的歌剧《唐·卡洛》中菲利普二世的咏叹调,他的声音很好,但音乐表现上很平庸。
栾:我记得他一上来就这样唱,把菲利普二世深夜在寝宫中的内心独白唱的很响,这个乐句应该一开口就控制好力度,唱出菲利普内心的一种感觉。(他用接近半声的力度示范这一句)
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学声乐的人唱歌时的状态不自然,外观让人看上去很不舒服。
栾:我也见过这种人,歌唱时狂张大嘴,歌唱形象很难看。也曾有人问过我,唱歌时嘴到底是竖着张还是横着张?这没有什么绝对的横着和竖着,要看是什么元音,是在什么高度上,横着张的口型应该是更科学一点,因为我们说话时没有哪个字是可以把嘴竖起来说的。人民音乐出版社曾出过一本介绍卡鲁索的书,书的全名我记不太清楚了?
田:叫《卡鲁索的发声方法》。
栾:对!就是这本书,在书的最后面几页,有卡鲁索怎样唱a e i o u的口型照片,不知你看过没有田兄?那可是卡鲁索的嘴哟、世界顶级的、最具权威的歌唱家,他的医生把卡鲁索发a e i o u的X光图片,牙齿结构和嘴是怎么张的都告诉你了,没有一个元音是这样竖着张的吧?我认为这是一本有用的书。
田:我特别推崇这本书,经常给学生看那些照片。因为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学生,他们不知道嘴到底应该怎么张,常常是用一种固定的口型唱歌。由此可见,在我们的声乐教学上,有些声乐教师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栾:这本书可以说是歌唱的,我买了很多送给能读懂它的学生们,能做到怎么说就怎么唱,我想应该是到了够段位的歌唱家了。(此时播音员报告飞机开始下降,我们只好终止了交谈)
田:谢谢你能这样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告诉大家!
栾:很高兴,也谢谢你田兄!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欢迎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