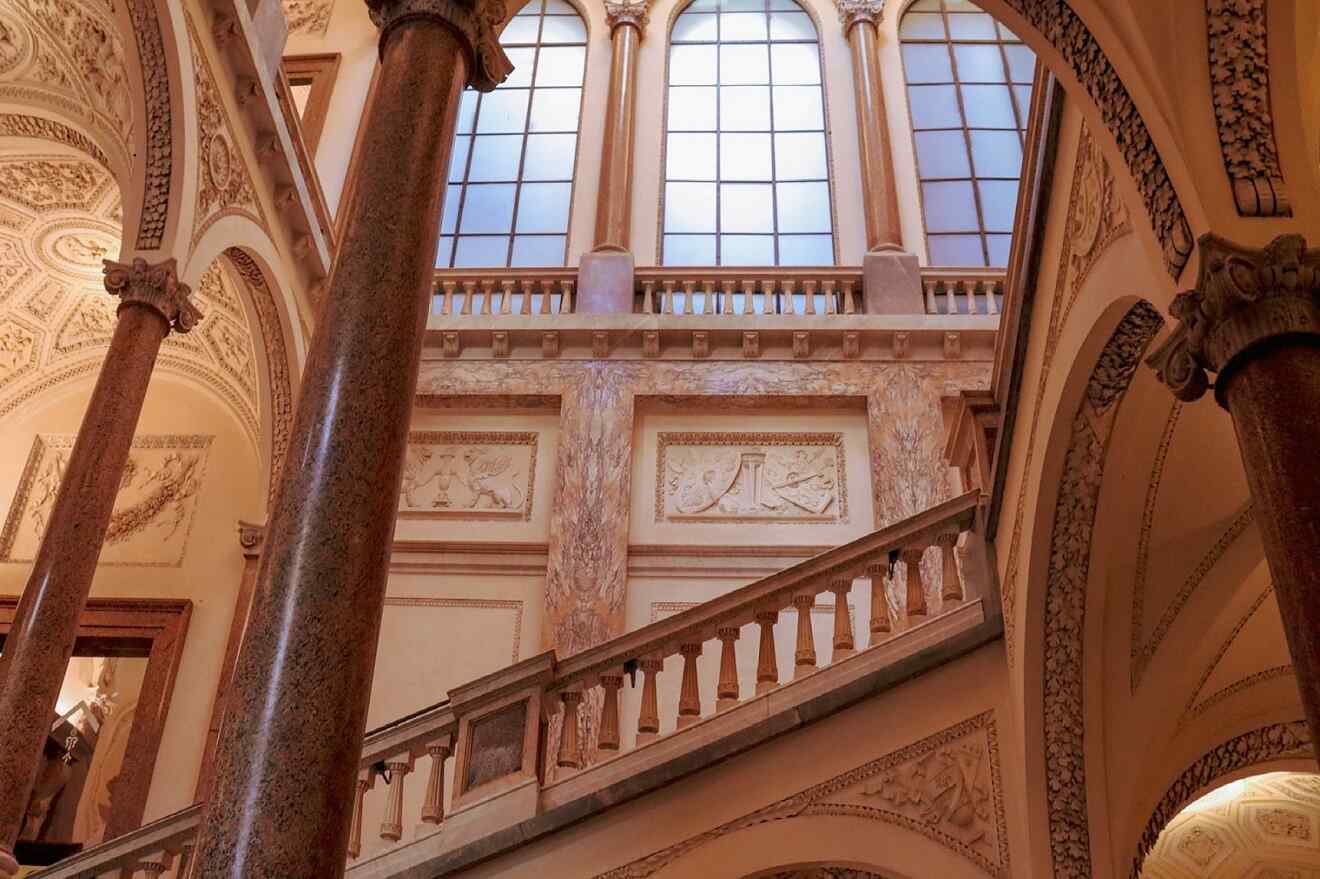1997年4月,我到挪威奥斯陆大学做三个月的访问学者。接待我的是北欧汉学界的大腕级人物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先生。何先生是挪威科学院院士,李约瑟《中国科技史》语言逻辑分册的作者,他的地窖里装满了中国古代的黄色书籍。不过更重要的是,何先生会吹长笛。
一进何先生家,心中不由得大喜。一楼的大客厅中摆满了许多乐器,西洋的不去说了,二胡笛子也赫然摆在关公的雕像旁。慈眉善目的何太太是一个业余中提琴手,每星期参加两次家庭音乐会,一次在自己家,一次在朋友家,雷打不动。
我到奥斯陆的那一天,正好何太太在练德沃夏克的“特兹”三重奏。我说“特兹”的第一句最亲切,何太太笑笑,操起琴就把那句顺手拉了一遍。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我说到我父亲是德沃夏克迷,我是吉他迷。何太太马上递给我一把吉他。我吃了一惊,因为我起码有六年没怎么碰过吉他了。但是这把吉他实在很趁手,音色也好,我拨来拨去,连滚带爬地也就弹了一段塔雷加的《阿迪丽达》。何太太听完了对何先生说:
“就让他住在我们家吧。”于是我就在何先生家住了三个月。
平常吃晚饭是在8点钟,到了朋友来奏室内乐的那一天就要提前到6点钟。到了晚上,朋友们来了。他们的搭配并不总是固定的,有时候来两个人,有时候来三四个人。我最经常见到的是一个叫叶特的说话细声细气的小个儿邻居老太太,颤巍巍背一把同她个头儿差不多高的大提琴。
他们在楼下客厅里拉琴,我因为还是生客,就躲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听。第一次除了“特兹”外,还拉了很多东西,我听得出来的有莫扎特《G大调四重奏》的一个乐章,海顿《C大调四重奏》的一个乐章。除了“特兹”以外,其他的曲子都是磕磕碰碰,拉拉停停,而且音准似乎也有相当严重的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每次都带一大堆乐谱来,除了事先约定的一首曲子以外,其他的都是临时随心所欲地视奏。等送走朋友们后,何太太问我他们拉得怎么样,我支支吾吾地说:“你们奏的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何太太笑了,她说天下最有趣的事就是在家里同朋友们一起拉室内乐,但是家里的其他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一块儿加进来演奏,要么就躲到地下室去。我说我父亲也表达过类似的渴望,可惜他的朋友和儿子们都很不争气。知音已然难觅,愿意一起来拉室内乐的多少年也没粗一个。不过,我这次到挪威是一定要帮助他弥补这个缺憾。我准备买一台专业的电脑合成器来代替他一直没有找到的合奏伙伴。
我到挪威的第三天,主人就请我到外面去听音乐了。这是挪威国家音乐学院的学生举办的音乐会,每个星期至少也有两三次,而且全是免费的!第一次我是同何夫人一块儿去的,到了那里一看,当天晚上同时有两场音乐会,一个是勃拉姆斯的《德语安魂曲》,在学院的大音乐厅;另一个是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单簧管五重奏,在小厅。这可是鱼和熊掌啊。最后还是决定去听五重奏。
虽然是非正式非盈利的演出,却也印有漂亮的节目单。因为去得早,我平生第一次做上了音乐会第一排的位置,后来的感觉是好像大提琴的弓子都要戳到我的鼻子上来似的。一个穿牛仔裤的姑娘过来上蜡烛,把厅里的大灯灭掉,然后我平生最喜欢的两支五重奏就在一片宁静的金色光中开始了。
这几个音乐学院的大学生把这两首曲子都奏得激情澎湃,据我看来当然是大错特错。但是整个音乐会的气氛实在是太好,而且离演奏者如此之近也有不可思议的效果,好像人真的就在音乐“里面”似的。看了,就室内乐而言,与其在音乐会大厅遥远的地方听大师们隔靴搔痒,倒还不如到这个小厅中来听几个初出茅庐的姑娘小伙子们性情中的演绎。
过了几天,何夫人又请我一起去听舒伯特音乐会,这一次是在一个民俗博物馆的三楼,票价60克朗(1克朗值1块多一点人民币),比起两三百克朗的正式音乐会票价,这应该算是便宜的。何夫人手上有一大把这种廉价(包括免费)音乐会的信息。在奥斯陆这个人口不到上海二十分之一的小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每天都在外面找的各式各样的音乐会。我必须适可而止,否则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了。我之所以同意赴这场音乐会,是因为这里面有我慕名已久而又闻所未闻的几首歌,是舒伯特专为几天创作的。
我发现每逢这种不对号入座的音乐会,何夫人总是要早到一刻钟,好抢占第一排的位置。这个博物馆的一楼正在举办摩托车展览,我看到了比一座房子还大的摩托车。奇怪的是音乐会的票子在一楼就被收掉了,那么看摩托车的人也可以到三楼去听音乐喽?
上半场音乐会的主角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声乐家。在音乐会开始前,他进行了一番漫长的说白,把大伙儿逗得哄堂大笑。我当然是一个字也听不明白。我后来发现这几乎是当地音乐会的一套固定程式。在每唱一首歌前,他先要把这首歌的歌词声情并茂地朗诵一遍,令我想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前的音乐欣赏节目。吉他伴奏的舒伯特歌曲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觉得他把伴奏部分写得像独奏那么难,看看那个弹吉他的小伙子气喘吁吁的样子就知道了。
何太太是个真正的乐迷。有一天傍晚从奥斯陆大学回到何先生家里,何先生抱怨说,何太太扔下我们不管了,晚饭也不做了,让我们自己看着办吧,她到国家剧院门口去了,去等人家的退票,家里有一个乐迷做太太真是太不幸了。
但是何先生自己也是一个乐迷,有一次他从芝加哥大学讲学回来,带回来菲利普版罗马尼亚女钢琴家哈斯基尔的简装(他们总是买便宜货)纪念专辑,没日没夜地放。他说他从小就是哈斯基尔迷,他做牧师的父亲更是五体投地的哈斯基尔崇拜者。何先生痛恨一切拿腔作调的滥情的演奏风格。在挪威期间,他的这种口味多少对我发生了一些影响。
有一次,我们听完一张哈斯基尔弹的“悲怆”和莫扎特K330的唱片,我忍不住大放厥词,说这张唱片总哈氏的“悲怆”轻飘飘的,味同嚼蜡,看来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弹贝多芬。至于330呢,第一乐章也弹得一般,但是第二乐章却处理得妙不可言,令人有渐入佳境之感。
听完我的这番高论,何先生大吃一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几十年前,他那做牧师的父亲就这张唱片说过同我几乎完全一模一样的话。如今菲利普的唱片只不过是当年的翻版而已。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差点要笑昏过去。
何先生家经常来客人,像贺友直啦,叶君健啦等等。在5月份的时候,他家里又多了一个人,从比利时来了一个研究韩非子的博士研究生,要在他家住两个星期,由何先生当面指导毕业论文的写作。又过了几天,何先生家开始沸腾起来,因为研究生的丈夫要来了,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音乐家,名字叫托姆。托姆博士的专长是用“历史钢琴”演奏海顿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这次他带来了两张他刚用“历史钢琴”灌录的唱片,是从唱片公司直接拿过来的母盘。据他说除了制作者外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听过。一张是舒伯特等人的艺术歌曲;另一张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其中“悲怆”用1798年的钢琴演奏,“111”用1804年的维也纳钢琴演奏。
托姆一手不停地摁着CD机的快进键,一边放一边为我们作解说。这两张母片不能像通常的CD那样检索,必须凭感觉和记忆来播放,实在是非常麻烦。“历史钢琴”的音色偏于干瘪和黯淡,一开始很难叫人习惯,但是用来为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伴奏倒似乎是比现代钢琴更为体贴——不错。我又想到了心爱的吉他,“历史钢琴”的音色就是由一点点像吉他,作为伴奏是绝对不会喧宾夺主的。
但是托姆演奏的贝多芬的“悲怆”却让我惊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不是“历史钢琴”,而是他对贝多芬的诠释。“悲怆”我少说也听过有20编,我还弹过塔雷加为吉他改编的第二乐章,谱子到今天也还能背下来一半,但是从来没听过像托姆这样大胆而放肆的演奏。这是一种滑稽的、歇斯底里的、抽筋似的风格。“每一句都绝对忠实于贝多芬原貌。”托姆说。
我应该相信托姆吗?他是音乐学院的教授,当年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演奏,应该是无一字无来历的了。但是这样的贝多芬也实在是太离谱了。在我的想象中,音乐学院的教授弹起钢琴来应该是一板一眼、循规蹈矩、毫无激情可言的。大错特错。照托姆说来,越是严肃的研究者,弹起琴来就越自由。
无论如何,托姆的演奏生气勃勃,令人耳目一新。而他演奏的“111”更是第一次让我享受了贝多芬晚期奏鸣曲的无穷魅力。对于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怪物,我从前一次次地硬着头皮反复细听,像大名鼎鼎的“106”,我曾经从“中图”买来磁带一口气连着听了三遍(我一直迷信反复聆听是接近艰深曲目的不二法门),但是几乎毫无效果,只能怪自己道行太浅。
“111”我从前至多听过一遍,而且完全莫名其妙。虽然对托姆的“悲怆”仍然满腹狐疑,但是下面他弹的“111”则令我狂喜,而且在毫无对比的情况下(也许正是太多的对比干扰了我对他处理的“悲怆”的欣赏?),我倾向于认为这就是贝多芬所愿意听到的处理:第一乐章狂躁而又郁闷,充满了反讽式的激情,而第二乐章在中间部分出现了似乎是用竖琴演奏出来的极为温柔美妙的琶音,这种音乐仿佛是托姆把自己的手伸进“历史钢琴”的内部,在那些“历史”的琴弦上轻轻地抚摸出来的。实在是太精彩了。
回国以后,我赶紧找来两个版本的“111”,其中还有一个是布伦德尔的,但是,却再也找不到那天同托姆一起欣赏时的那种极度快乐的感觉了。他们的演奏比起托姆来差得太远,要么就是我先入为主的意念太强烈。
托姆过去差不多只弹海顿和贝多芬。我问他以后还想不想弹其他人的作品,他说下一步想弹洪美尔的曲子。我说我很喜欢洪美尔的钢琴三重奏,他的《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简直就像是贝多芬和莫扎特联手合作写出来的。但是他的《升F小调钢琴奏鸣曲》的开头是不是有无调性音乐的味道?
这回轮到托姆睁大眼睛了。他说,洪美尔是一个差不多完全被人遗忘的名字。他的作品几乎从来没有出过唱片,你又是从哪里听来的呢?我说我从互联网上一个叫做“古典音乐档案”的地方下载过这上面所有的洪美尔作品的MIDI文件(我自己都奇怪为什么会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中选择洪美尔),然后在自己的合成器把它们放出来。我还有克莱门蒂和迪亚贝利的奏鸣曲呢,可不是它们的小奏鸣曲!
可怜的托姆完全不知道什么叫MIDI(在中国谁不知道MIDI?)。他说他弹过电子钢琴,那玩意儿是一个笑话,触键和音色完全不对头。他、何先生、何太太对于我的合成器情结和互联网狂热完全不能理解,一有机会就要加以猛烈的攻击。何先生老是说,像我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整天泡在网络上,像烟鬼渴望鸦片那样地迷恋毫无人性的机器,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应该去弹吉他才是正经。
有时候我晚上躺在床上,会迷迷糊糊地想起何先生的话,也许他是对的。
原刊《音乐爱好者》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