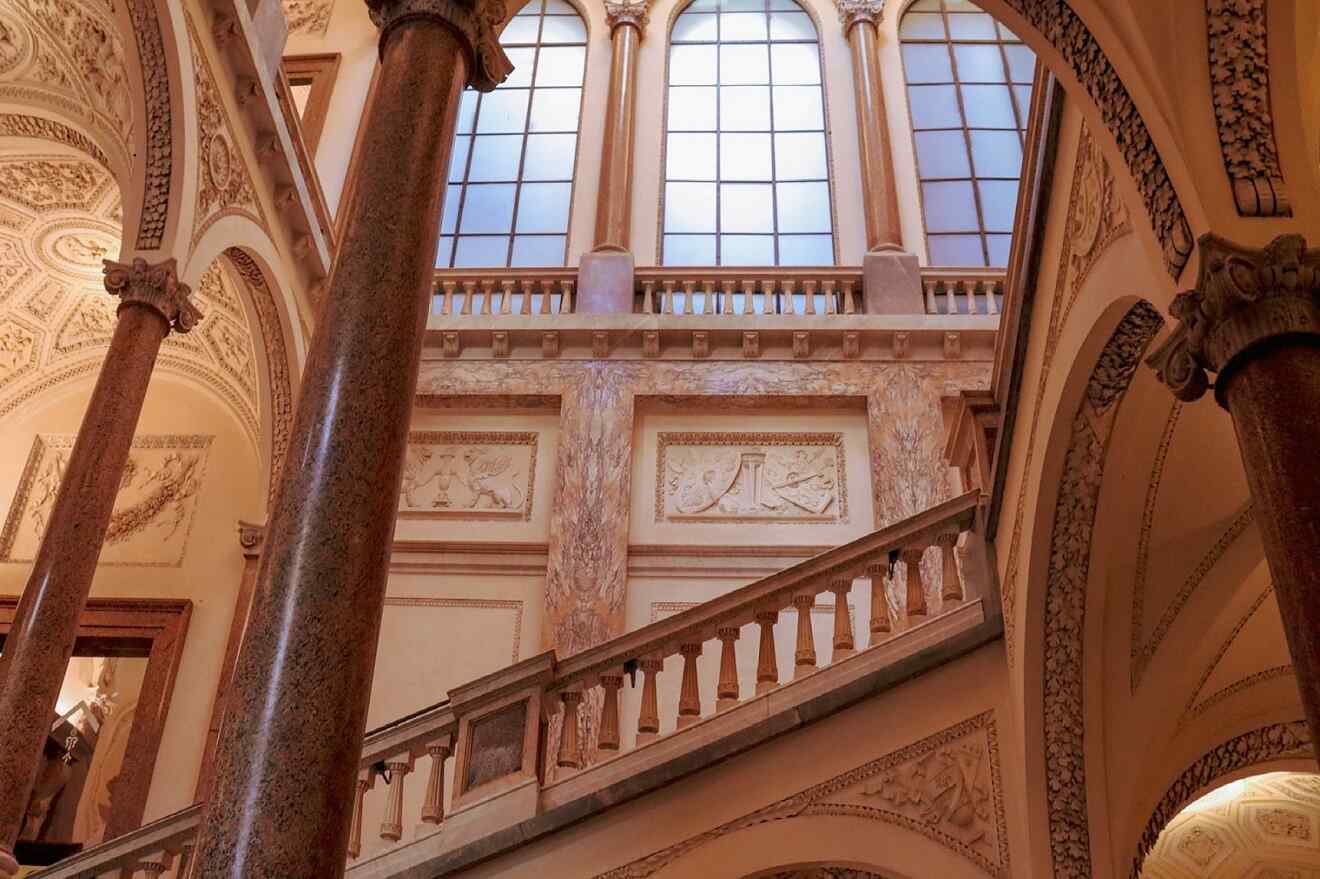郎朗《土耳其进行曲》
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自幼就表现出超常的音乐天赋,3岁练琴,5岁作曲,1762年起其父安排去欧洲各国宫廷表演,1763年起作更广泛的旅行演出,在路易十五的凡尔赛宫逗留了两周。
1764年到达伦敦,受乔治三世接见,在伦敦曾师从阿尔贝尔与J.C.巴赫,创作了最早的3部交响曲。1766年莫扎特全家返回萨尔茨堡。1767年与1768年两次再访维也纳,创作了早期的两部歌剧。1769年底,其父又带他到意大利,其后不久又两次访意。莫扎特的早期创作基本都是在其父母带他到欧洲各国巡回演出中的创作习作,这期间他广采各家之所作,锻炼了极强的适应各种创作的能力。在莫扎特的早期创作,主要受J.C.巴赫的创作的影响。1778年,莫扎特到巴黎,7月其母去世,其时法国人已对作为神童的莫扎特不感兴趣,莫扎特求宫廷职务不成,只得返回萨尔茨堡,担任宫廷与教堂的管风琴师,因与大主教不和终于辞职去维也纳。
1782年起莫扎特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期,1782年8月,他创作了《后宫诱逃》,然后与康斯坦策.韦伯结婚。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大量最有光彩,也最具他特色的作品。在维也纳宫廷担任乐师期间,他创作了大量为宫廷服务的舞曲、嬉游曲、小夜曲;他和迪特斯多夫和海顿一起拉弦乐四重奏,担任中提琴手,创作了非常重要的《海顿四重奏》,另还有各种类型最优秀的协奏曲与室内乐。
1788年后可看作莫扎特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晚期。这一阶段一方面他创作出巅峰作品,比如最后的3部交响曲、歌剧《女人心》、与《魔笛》;另一方面,他的创作中也开始出现了较激烈的,在晚期的室内乐作品、作品中,这种表现得特别明显。
莫扎特一生共600多首作品,对各类音乐体裁创作都能轻松自如。他的创作特色:
其一,靠其天才而体现出的优秀的即兴性。
莫扎特大量的创作都是即兴灵感发挥的产物,他的优秀的即兴感觉能力无人能与之比拟。
其二,他的音乐中所体现出来的即兴的单纯的美,不是精雕细琢的产物,所以呈现着一种自然的单纯;因为保持着孩子般的单纯,其音乐中似乎没有杂质。
其三,非凡的平衡能力。
莫扎特音乐基本承袭了从巴赫到海顿那种创作是体现音乐中各种因素的平衡的能力,莫扎特的长处是善于在丰富的音乐灵感的表现中自然地达到出色的平衡。
其四,把宫廷艺术的优雅发展到了顶峰。
莫扎特的音乐植根于萨尔茨堡和维也纳文化之中,莫扎特的音乐是最单纯、最自然、最优雅、最宁静的音乐。莫扎特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乐器歌唱,他把过去时代伟大声乐艺术中的抒情性,注入他的精美的器乐形式中。莫扎特既没有从民歌也没有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他的音乐严格说是室内的音乐。
在莫扎特的音乐中,他创作的歌剧丰富了德国歌剧的形式,也推动了其它形式发展。在歌剧创作中,较全面地体现了他在生活中的欢乐、忧伤及他个性多方面的冲动。给莫扎特撰写了3部歌剧的达·庞特称,莫扎特的歌剧是“忠实地用全部色彩描绘各种激情。”
——林逸聪《音乐》
“莫扎特并不想说什么,他只是唱歌,只是传出声音。因此,他并不强加给听众什么,也不要求他们作出决断或者表明态度,而是让他们感到自由。”“主观的自我从来不是他的主题。他从不利用音乐来解释自我、解释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情绪。”“他的使命便是使自己完全摆脱掉他的重大和细微的生活体验,一次再一次地帮助他生活于其中的音响宇宙中的一小块变成形体。”“借助此一转化的力量,光明上升,阴影下沉而又不致消失;欢乐超越痛苦而又不解除痛苦。”个人觉得只读巴特的第一篇便足够,曾一直拿莫扎特和歌德与拉斐尔作比,现在想想,确实是忽略了“莫扎特的自由”。
——评论《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
今天推荐的CD封面,聆听点击阅读原文
专辑简介:《莫扎特》当国际钢琴巨星遇见先锋指挥家,首张全莫扎特作品集震撼发行。CD1收录郎朗与哈农库特以及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录制的G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和C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CD2收录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土耳其进行曲及F大调小品的四则钢琴选段。国际钢琴巨星郎朗最新专辑《莫扎特》是郎朗首张全莫扎特作品集。专辑中,郎朗与实验音乐先锋尼古拉斯.哈农库特(Nikolaus Harnoncourt)和维也纳爱乐乐团(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倾情合作。哈农库特,奥地利本土指挥大师,擅长指挥前浪漫主义时期以及巴洛克时期的古典音乐作品,音乐风格原汁原味独具特色。谈到这位极具代表性的指挥家,郎朗说到,“和他工作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他非常值得信赖。他有独特的诠释音乐的方法,带领我回到当年莫扎特创作这些音乐时的感觉。”对于哈农库特来说,这同样也是一次非常富有激情的合作,“很难遇到像(郎朗)这样想法开阔的人,通常与我合作的演奏家都是准备好了要与我演绎某个主题,但这次(和郎朗)合作我们磨合非常迅速,这非常少见。”今年春天,郎朗与哈农库特以及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录制了专辑CD 1的曲目,在哈库特的指挥下,完成了G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和C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的录制。CD 2的曲目则是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土耳其进行曲、F大调小品的四则钢琴选段。莫扎特奏鸣曲同时也是正在进行的郎朗世界巡演的曲目。
CD1
01 Piano Concerto No.24 in C Minor, K.491 I.Allegro
C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快板
02 Piano Concerto No.24 in C Minor, K.491 II.Larghetto
C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小广板
03 Piano Concerto No.24 in C Minor, K.491 III.Allegretto
C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 第三乐章:小快板
04 Piano Concerto No.17 in G Major, K.453 I.Allegro
G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快板
05 Piano Concerto No.17 in G Major, K.453 II.Andante
G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行板
06 Piano Concerto No.17 in G Major, K.453 III.Allegretto - Presto
G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 第三乐章:小快板 – 急板
CD2
01 Piano Sonata No.5 in G Major, K.283 I.Allegro
G大调第5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快板
02 Piano Sonata No.5 in G Major, K.283 II.Andante
G大调第5号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行板
03 Piano Sonata No.5 in G Major, K.283 III.Presto
G大调第5号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急板
04 Piano Sonata No.4 in E-Flat Major, K.282 I.Adagio
降E大调第4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柔板
05 Piano Sonata No.4 in E-Flat Major, K.282 II.Menuetto I - II
降E大调第4号钢琴奏鸣曲 第二乐章:小步舞曲I&II
06 Piano Sonata No.4 in E-Flat Major, K.282 III.Allegretto
降E大调第4号钢琴奏鸣曲 第三乐章:小快板
07 Piano Sonata No.8 in A Minor, K.310 I.Allegro maestoso
A小调第8号钢琴奏鸣曲 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
08 Piano Sonata No.8 in A Minor, K.310 II.Andante cantabile con espressivo
A小调第8号钢琴奏鸣曲 第二乐章:富于表情的,如歌的行板
09 Piano Sonata No.8 in A Minor, K.310 III.Presto
A小调第8号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急板
10 March In C Major, K.408/1 1号进行曲
11 Piano Piece In F Major, K.33b
F大调小品
12 Allegro For Piano In F Major, K.1c
F大调钢琴快板
13 [Rondo] Alla Turca .Allegretto (From Piano Sonata No.11)
A大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 第三乐章:土耳其风格-小快板(土耳其进行曲)
风in:莫扎特的音乐辩证法
“嬉戏”(P25)是莫扎特音乐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理解其音乐的关键角度,但这种嬉戏并不是无原则的跳跃,更不是无节制的狂欢。相反,它有着内在的张弛与平衡,它是“法则约束下的”自我,是一种符合“中道"精神的"音乐辩证法(P55),就像卡尔·巴特所言:“它摆脱了一切夸张、一切原则上的突变和对立。阳光照耀着,但不刺目,不消蚀人,不炙伤人;天穹披覆着大地,但却不给它重负、不积压它、不吞噬它。”(P29)于是,在莫扎特的指引下,音乐、自由和听者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这种默契可以是泪痕未干的笑脸,也可以是眉头渐开的哀怨;可以是暖阳高照的雪地,也可以是雷声阵阵的静谧。在这样的世界里,“光明上升,阴影下沉而又不至消失;欢乐超越痛苦而又不解除痛苦;‘是’高过于‘非’,而‘非’又仍任存在着”(P30),一切都自由而本真。汉斯·昆认为莫扎特的音乐是一种“超验的艺术”,它有着“超越理性(无论是批判理性还是神学理性)后的宁静”(P68)。然而对我们更多人来说,正是这种符合“中道”的自由与本真才构成了莫扎特音乐最宝贵的品格,而这或许也正是莫氏音乐的"神性"之所在。
——引文出自《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
PS:今天公众号贴得音乐全都是土耳其进行曲,也就是钢琴奏鸣曲K331的第三乐章,这首曲子重复体现了莫扎特作品的“嬉戏”特征。
《土耳其进行曲》是莫扎特《A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K331)中的第三乐章。第一乐章是“文雅的行板”,第二乐章是“小步舞曲”,第三乐章就是《土耳其进行曲》。1777年,莫扎特进行第二次旅行演出时,与音乐家韦伯(浪漫主义音乐家)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使他的创作思想更加成熟,并在器乐创作中显露出成熟的创作风格,这点特点表现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中。A大调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1778年写于巴黎的作品(当时他才22岁)。莫扎特共写了十九首钢琴奏鸣曲,这些奏鸣曲都显示出明朗乐观的乐思,完美匀称的结构和严谨如歌的旋律等创作特征。《A大调钢琴奏鸣曲》是其中的第十一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
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巴洛克时期(1600年至1750年)的华丽,精致,炫耀,追求对比强烈而略带夸张。巴洛克艺术尽管有呆板的礼仪,有形式上的骄矜和夸张,但它毕竟是一个阳刚的时期。紧随其后的时期,即洛可可艺术。洛可可艺术是法国十八世纪的艺术样式,发端于路易十四(1643~1715)时代晚期,流行于路易十五(1715~1774)时代,风格纤巧、精美、浮华、繁琐,又称「路易十五式」。艺术的风格,在音乐家莫扎特、海顿,文学家蒲伯、爱迪生、伏尔泰,画家华铎、康斯博罗中,贯穿着一种共同主题,它把理性与优美,趣味同轻松、明晰、秩序井然的材料相互配合起来。路易十四常在凡尔赛宫开各种舞会,借着繁琐的礼仪与无意义的职务折腾贵族们,再以富丽堂皇的宫廷装饰营造悠闲的环境,有利搞风流韵事,以便消耗贵族们的精力,。因此艺术家授命编造一种理想生活的极乐世界情景,其唯一的目的是塑造出一个悠闲的、实际上是懒惰的社会快乐。
当时一些欧洲作曲家对异国风味的音乐发生了兴趣,而莫扎特在他的《A大调钢琴奏鸣曲》里,也写了一段异国风味的曲调作为第三乐章。他在这段曲子前面,标有“土耳其风”几个字,《土耳其进行曲》因此而得名。这首乐曲的土耳其风格并不浓郁, 和真正的土耳其音乐的节奏、音调相差甚远。这首乐曲的曲调流畅动听, 技巧也不难, 所以受到人们的喜欢而经常被拿出来单独演奏, 反而比《A大调钢琴奏鸣曲》更有名气。
《土耳其进行曲》表达的是一种欢快,清新,而又典雅,优美的情绪,是个体快乐与贵族优雅感的结合,是一种优雅的快乐。演奏这首曲目,虽然技巧不难,但是情绪的把握却相当不易。弹得太快,太重,太放,就会显得欢快过头,欢快到放肆,优雅感就会被弱化掉。弹得太紧,太收,又会显得谨慎有余而欢乐不足。所以在弹奏的力度,速度,收放度上都必须达到一个平衡。欢快是什么?欢声笑语,轻舞飞扬。表现在钢琴弹奏上,是跳跃的节奏,是短促宛转的力度和速度。而优雅呢?贵族的社交活动是限制于礼仪框架内的,比如鞠躬时女士要弯膝提裙角,舞蹈时手放哪脚放在哪步伐多大都有规矩,说话时不能大声等等。表现在钢琴的弹奏上,就是速度不能太快,力度不能太大,节奏不能慌乱,就好比有一个框架限制着弹奏者的双手一样。要弹奏出优雅的感觉,手的各种动作都必须在这个优雅的框架之内。而同时要想表现出欢快,就得在这个框架中寻求尽量最快的速度,合适的力度和节奏。所以练习这个曲目最好是先找到优雅的感觉再去摸索欢乐的情绪,也就是先勾勒出优雅的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里面渲染出欢快的情绪。
郎朗:有段时间我不敢弹莫扎特
本报讯(记者罗颖)在2015年1月新年档期上映的多部电影中,有一部非常特别的影片,这部影片的主角是著名钢琴家郎朗,影片的内容是他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独奏音乐会的现场,这部名为《热情奏鸣曲》的影片是时下在欧美非常流行的音乐会电影,而在中国还是首部进入全国院线放映的音乐会电影,郎朗也成为首位发行音乐会电影的古典音乐家。
昨天, 一直在国外巡演的郎朗出现在北京,为媒体朋友和乐迷介绍这部特别的电影。这部由库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的《热情奏鸣曲》,真实细腻地记录了郎朗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独奏音乐会,曲目包括贝多芬两部著名奏鸣曲及肖邦的几首著名乐曲。对于音乐会电影,郎朗本人早已熟悉,“当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时,经常在学院的小礼堂通过大屏幕看卡拉扬、伯恩斯坦等乐坛大腕的音乐会现场录影,学习到很多对作品的诠释方法,令我受益匪浅。”郎朗表示在电视上最多弹5分钟,属于半娱乐化的表演,电影音乐会有一个半小时,足够让大家仔细听一部作品,这部电影又由16个机位拍摄而成,并进行了专业的后期剪辑,对于学习音乐的孩子,看这样的音乐会电影将事半功倍,“看音乐会现场时,家长大多让孩子紧紧盯着音乐家的手指,但是音乐会电影在导演丰富的经验执导下和镜头的引导下,能让孩子看到更多音乐诠释的角度和细节,比现场更近距离地感受到音乐会的每个感人片段,再现了古典音乐的魅力。”
昨天,郎朗还带来了自己的最新专辑《莫扎特》,和所有从小就学音乐的孩子一样,郎朗也是在莫扎特的围绕中长大的,莫扎特传奇的人生对郎朗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有吸引力,但是在弹奏莫扎特的音乐上,曾经给郎朗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莫扎特真的很难弹,弹复杂了不是莫扎特,弹简单了觉得无聊,尺度很难把握,这令我非常苦恼,有段时间我根本不弹莫扎特了,尤其是刚来北京上学时弹莫扎特A小调奏鸣曲,总是没弹明白,老师因此就不教我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郎朗回忆。直到17岁见到著名指挥大师和钢琴家艾森巴赫,郎朗才对莫扎特有了重新认识,“艾森巴赫问我,你的作品什么都有,怎么没有莫扎特,我说莫扎特太难了,于是艾森巴赫邀请我一起弹莫扎特的四手联弹作品,我负责很简单的低音部分,在演奏时我突然觉得音乐怎么这么美,有这么多音色和踏板的变化,这才是莫扎特!这次之后我终于突破了自己的心理防线,喜欢上了莫扎特。”
李云迪、周杰伦《土耳其进行曲》
中译本前言
莫扎特
我与莫扎特
致莫扎特的感谢信
莫扎特评说
论莫扎特的自由
莫扎特:超验的踪迹
引 言
超验的踪迹――对莫扎特音乐的体验
一、?
二、性的?
三、神性的?
四、人性的、太人性的
五、奥秘
六、幸福感
七、结语:超验的踪迹
人民的鸦片?
――对莫扎特的《加冕弥撒曲》的神学思考
时代背景
《慈悲经》
《荣耀颂》
《信经曲》
《圣哉经》
《羔羊经》
莫扎特在欧洲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不仅音乐创作史如此——柴柯夫斯基和马勒都把他奉若神明,思想史上的影响同样如此。
本书提供了莫扎特音乐与神学的关系的两份现代文献:一,现代神学泰斗卡尔·巴特在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时写的几篇隽永的随笔;二,。与欧洲音乐的关系,并非仅体现在欧洲音乐史上至今仍在发展的性作品,也体现在神学家对音乐的沉思——施韦策尔曾写过五十多万言的巴赫研究。
巴特的几篇短文虽属杂性质,却透露出他的思想中一些颇为独特的方面,例如,他把莫扎特的弥撒曲与自己卷帙浩瀚的教义学联系起来:两者的本质都是堂皇上的荣耀。这些小随笔不仅令人赏心悦目,也是研究巴特思想的有学术价值的资料。
汉斯·昆的两篇论文则有相当的学术性,分别讨论两个有关联的问题:第一,,其音乐作品的属性是什么,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昆试图解答;第二,通过对莫扎特弥撒曲的神学解析,昆致力说明莫扎特音乐的信仰的品质。
收入本书的第三篇作品,出自音乐家之笔。不过,居尔克并非一般的音乐家,应该说,他是学者、诗人型的音乐家。居尔克出生于魏玛,早年主修大提琴、德语古典文学和哲学,分别在耶纳大学和莱比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和大学教授资格。
一个人,巴特说,不论何时听莫扎特的音乐,都将被置于“一个美好而又有秩序的世界的门槛之前,这个世界不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雷雨交加之时,不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保持其美好和秩序,而我作为20世纪的人,每次都从中获得勇气(而非傲气),获得速度(而非超速),获得纯洁(而非单纯的纯净),获得安谧(而非懒散的静止)”。是的,有莫扎特的“音乐辩证法萦绕耳际”,人们“既可以使青春永驻,也能够宣泄悲伤,一言以蔽之:人们能够生活”。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在巴特的莫扎特作品解释中,人们听到的正是莫扎特音乐本身所表现的“高于否定的肯定”。
我们应预先说明,,。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成为会员,,而且只可能通过这类圣事达到的观点肯定毫无影响。因此,他可能并不喜欢我们新教徒,据说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过分在意我们的了(“其中可能有某些真实性,但我不知道”)!茨温利也许给这位在奇妙的氛围中生活的人指引过一条特殊捷径去接近亲爱的上帝,要知道他甚至也为形形色色虔诚的异教徒确定过这样一些捷径。无论如何,人们必须考虑到,亲爱的上帝有一条接近莫扎特的特殊捷径。“有耳朵可以听的,都听吧!”(可4:9)
不过,人们万万不可以认为,认知我们讨论的人和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莫扎特丰富多彩的作品与短促而动荡的一生蕴含着一个解不开的算式,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秘密。必须看到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莫扎特的音乐(以及他的音乐所体现的他的人格)至今仍然如此激动人心。
如果谁对莫扎特仅一知半解就试图去讨论他,谁就很容易停留在仅仅用一些溢美之词去赞美他的阶段。基尔克果就是一例。他曾以威胁的口吻扬言,他将游说“从教堂司事到红衣主教的全体神职人员”,敦促他们承认莫扎特胜过所有伟大人物,否则,他将“退出他们的信仰”,与之决裂并建立一个“不仅尊莫扎特为至高至上者,而且只敬奉莫扎特一人”的教派。稳健持重的歌德不也是称莫扎特是音乐中高不可攀的“奇迹”吗?其他无数知名度稍逊的人更是如此,他们在将莫扎特与其前后的大师们作坦诚比较中进行评论时,心中想到的、嘴里说出的不也尽是“绝无仅有的”、“无可比拟的”、“至善至美的”这类词藻吗?当然,这些评价是比较准确的,只是也许有人会问:其本意究竞何在?这就是说,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人们口头上在称颂莫扎特,而意之所瞩却是贝多芬或舒伯特,因为他们的最高成就莫扎特在其晚期创作中早就已经达到了。或者说,在莫扎特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中就已经表现出了他从音乐上群星灿烂的18世纪所采纳的诸多风格形式中的一种。近代以来,人们作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即对他的全部作品(完全像对待《新约》和《旧约》那样!)就他创作的早期和晚期所接收和吸收的来自多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如来自约·塞·巴赫的儿子们以及约·塞·巴赫本人的影响,来自韩德尔、格鲁克、、意大利及法国的作曲家们的影响。他之“独一无二”是否恰恰在于他不可能、也不想成为革新者、革命者,不可能、也不愿意有任何特别之处,他只能、也希望在他那个时代的音乐长河之中并依靠这条长河而生活和创作?是否恰恰在于他只能、也希望将音乐当作他独有的本己之物而使之发出声响?他之“独一无二”是否恰恰在于他只能、也希望作为学生——正是因此而“无可比拟”地成为大师?这里重要的也许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音乐吧?莫扎持早期和晚期作品的那种不容与他人混淆的原初本音是否与音乐之原初本音完全相同?难道他以其超越时间的形式击中和拨动了音乐的此一原初本音?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很难甚至不可能精确地为莫扎特的音乐下定义?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在对自己或别人解释莫扎特其人时,便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无济于事的夸张词藻吗?
有人曾经说,他是一个孩子(甚至是“神性的”孩子),是一个用他的音乐对我们谈话的“永恒的少年”。他令人痛心的短暂生命可能是他获得此一称号的缘由;但还有另一些缘由,这便是他对一切实际事务(根据他姐姐对他的尖刻评语,尤其就他处理婚姻以及一切与钱有关的事情上)所表现出的明显的无知,他在与人交谈时,尤其在信件中总爱发一些幼稚可笑的噱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仍然如此。最令人惊奇的是,据可靠材料证明,他事实上最爱在严肃工作的时候调笑发噱。倘若人们将他看成是“孩子”(布克哈特曾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这是人们在对他进行思考;倘若他们想到这个真正掌握着艺术技巧并不断以新的创作使之日臻完美的人懂得,不可用他的艺术——真正从未如此!——给他的听众以重负,而是每次都重新让他们参与他自由的、可以说童稚的游戏,那么,他们对他的理解便深入了一步。倘若他们注意到他——如他们所说的——“真正像一个纯洁的孩子那样”能够“一口气地对着我们痛哭,对着我们大笑,而又不容我们询问其原因”,那么对他的理解便又深入了一步。现在,我想提请人们考虑的是,命运恰恰不容许莫扎特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孩子”。
他3岁时就开始弹钢琴,4岁时已经准确无误地弹奏短小乐曲,5岁能谱写小品;与此同时,他在父亲指导下不倦地学习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算术及许多音乐知识。他6岁时进行第一次旅行演出,7岁时开始第二次,即那次为时3年半的巡回演出(他到过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在返程中途经日内瓦、洛桑、伯尔尼、苏黎士、温特图尔、沙夫豪森!)。从14岁到17岁—这期问已经在持续不断地谱写歌剧、交响曲、弥撒曲、四重奏等——他曾三次去意大利巡回演出,而且从此便再也没有间断过羁旅生活。难道这是一个孩子?不,这是一个戴礼帽、佩短剑(歌德于1763年在法兰克福见到他时就是这副装束)、风度翩翩、永不休止地演出和创作的真正神童:他为伟大的玛丽亚·特蕾西亚、法国国王(不要忘记还有蓬巴杜夫人!)和英国国王所赏识和嘉奖,他接受专家们的考试,他被教皇克莱门斯14世授予“骑士”称号,并被波伦尼亚的一个音乐学术团体吸收为会员!这一切都离不开他严谨而练达的父亲的指导(在他心目中,父亲“仅次于上帝”)。在父亲看来,为了而发展儿子的“天才”和传扬儿子的“声名”(而且是在孩子本人完全同意和参与之下进行的)是正确和必要的。对于瑞士人,听起来最可怕的是:“沃尔菲尔”被完全剥夺或者说免除了入学读书此一善举!不然他会不堪其苦的!莫扎特不足36岁便因此而死于莫名疾患的病根大概应从他这种反常的青少年时代去寻找。不过,他当时没有变成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野孩子也算是一大奇迹了,其原因大概也是由于他没有时间去撒野吧。他从来不曾作过寻常意义上的孩子:正是付出此一代价,他方才成为另一种更高一层意义上的“孩子”。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否则便会作荒唐之想,发荒唐之言。
有一段时间,人们在说明莫扎特音乐时偏爱用“优美”或“欢快”这类词,并将他本人描绘为永远欢悦人心灵的洛可可的宣讲者,甚至称他为太阳神。一位瑞士人,与他同样早逝的名叫弗勒利希(F.Th.Frohlich,1803—1836)的阿劳的音乐总监称颂他是“一个欢乐童子”,“喜气洋洋的双颊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在“永远湛蓝的天空下”游荡着。但这不是莫扎特,既非他的生活,更非他的音乐。关于莫扎特是否“幸福”的问题,一个与莫扎特同时代并认识他本人的英国人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从来不曾幸福过。”当人们谈到他的音乐所具有的令人感到幸福的品格时,应该想到这一点!还有关于他的爱情的猜测(这远非是猜测):他虽然经常堕入情网,但他却从未真正爱过——除了音乐夫人——哪一个女性。另外,他与父亲日渐冷淡的关系,在萨尔茨堡大主教科洛拉多处供职时令人窒息的环境,此后在维也纳多次求职所遭受的挫折,家庭长期的经济窘迫,再加上病魔缠身等等,这一切都给他造成痛苦。莫扎特很爱笑,然而实际上这并非由于他有许多值得笑的事,而是因为他——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没有值得发笑的事仍然可以并能够笑。真实的情况是——这也许是莫扎特这个“欢乐童子”的童话的真实性之所在——他(如本世纪一位聪明的法国人所说)从不知怀疑为何物。这便是他的音乐所固有的激动人而又安抚人的性质。它显然是来自这样一个高层面,从此一高层面上(人们在那里将认知一切!)同时观察到了此在的右侧与左侧,即欢乐与悲痛、善与恶、生与死的现实及其局限。啊,我们善良的内格里(Hans Georg Nagli,谱写《最神圣之夜》的作曲家!),他竟因莫扎特作品所具有的如此鲜明的反差而在事后对他大张挞伐!人们怎么会因此而对他产生如此严重的误解呢?莫扎特不是开朗活泼的人,不是乐观主义者(他的明快悦耳的大调乐章、他的小夜曲和嬉游曲,甚至他的《费加罗》和《一切人全都如此》都无法证明他是这种人!)。但他也并非忧郁型的人,并非悲观主义者(他的大型和小型的8小调交响曲、d小调钢琴协奏曲、不协和音弦乐四重奏,以至他的《唐·乔万尼》的序曲和尾声都无法证明他是这种人!),他的音乐表现的是现实生活的,然而,尽管如此,其背景却是上帝的善良造物,因此(这大概便是关于他战无不胜的“优美”的议论所指的东西吧)而永远处于从左侧向右侧的转化之中,即处在从悲向欢、从恶向善、从死向生的转化之中而从不会逆向转化。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单调乏味的平野,也没有深奥莫测的绝地。他既不容许自己便宜行事,也不放任自己失去节律。他只是在一定的局限之内表现一切事物的真相。这就是他的音乐美妙、悦耳、动人之所在。我不知道另外还有谁的音乐值得人们作如此评说。
莫扎特音乐是包罗万有的,人们不禁为其中所表达的广泛内容而叹赏不已:苍天与大地、自然与人类、悲剧与喜剧、情感之各种形式的表露与深沉的内在宁静、圣母玛利亚与超凡的魔鬼、教堂大弥撒、的奇迹庆典与舞厅、笨伯与聪明人、懦夫与(真、假)英雄、忠诚者与奸佞小人、贵族与农夫、巴巴基诺与萨拉斯特洛。他似乎并不偏爱某些人、某些东西,而是爱一切人、一切东西:犹如普照一切的阳光,犹如浸润一切的雨蹬,这反映在——如果我没有听错话——他无限亲切、却又不似并非有意使然的风格之中。他总是以这种风格塑造和协调人的歌声或(在协奏曲中)主导的独奏乐器与伴奏的(不,通常绝不仅仅是伴奏的)弦乐器和管乐器之间的关系。人们百听不厌的不正是莫扎特乐队中那发生着、躁动着和激动着的东西?不正是那种种出人意料而又正当其时出现并以其特殊的高低音和音色而达到完美境界的东西?这一切不正是整个宇宙以缩微形式被表现于音响之中?显然,作为人的莫扎特听见了宇宙之音并使它——他自身只起媒介作用——歌唱起来。人们的确可以把这称之为“无可比拟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有待破解的谜。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表明,莫扎特事实上对他那个时代丰富的自然和历史科学、甚至对(除音乐以外的)艺术,如古典文学,根本不感兴趣。他有歌德的诗集,但他与歌德的关系只具体表现在为他那首《紫罗兰之歌》谱曲。他曾提到过诗人格勒特的逝世(在他童年时代写的一封信中将诗人写成格雷尔特),他还对——1777年在曼海姆与之匆忙认识的——诗人维兰德作过幽默的描绘。据我所知,这就是他留下的文献中关于当时的文学所记载的全部内容。他甚至根本不知道一个名叫康德(I.Kant)的同时代人的存在!在他的众多信件中,我不知道有哪封信曾谈到过他对故乡和他旅行过的国家的风光和建筑的深刻印象——可以说,全都是浮泛的描写。像默里克在他的著名中篇小说中关于莫扎特如何享受他的“布拉格之旅”的描写是诗人的创作而非生活的真实。因此,希望从对古老的萨尔茨堡及其周围环境的研究着手来理解莫扎特,这看来出于好心,但却是徒劳的。显然,,至少是不曾为之所动。在这里是否应提一下关于他的一段轶闻?据说,他6岁时在维也纳王宫光洁的地面险些跌跤,当时幸得一位同龄的玛丽·安托内特大公小姐,即后来不幸的法国王后的扶持。对这一扶持,莫扎特不假思索地立即提出结婚动议作为报答。事实上,他毕生所直接关注的——除了他变化不定的人事和职业关系——似乎只是与音乐有关的东西。问题是,从莫扎特的音乐看,他无所不知,至少像歌德那样博学,尽管他没有歌德那双全面观察自然、历史和艺术的眼睛;毫无疑问,他胜过历代千千万万比他读书更多的,即通常说的“更有学养的”、更有兴趣的通世事知人情者;那么,他从哪里得到这一切知识的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想必他所具有的某些感官使他事实上有能力冲破他那种古怪的表面上的封闭状态,摄取他显然善于表现的世间万象吧。
莫扎特音乐不同于巴赫,它不是福音;也有别于贝多芬,它不是生活理解。他的音乐并不宣讲学说,更不表现自我。人们沿着这两个方向从他的作品、尤其晚期作品中所作的种种发掘,在我看来,似乎带有极大的人为性,因而极少启发性。莫扎特并不想说什么,他只是歌唱,只是传出声音。因此,他并不强加给听众什么,也不要求他们作出决断或者表明态度,而是让他们感到自由。从他的音乐中所期待的欢乐是从人们接受这一事实开始的。他曾将人的死亡称作他日日思念的真正的好朋友。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果真是这么做的。然而,即便对这一点他也没有大事渲染,而只是让人去揣测。莫扎特也不想宣扬对上帝的赞美,而是实实在在地力行,这表现在他的谦恭态度之中: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件乐器,他只是让人去谛听他显然听见的东西,那是来自上帝造物浸润着他、在他心灵中升华,而现在又从他心灵中逸出的东西。
在这里,我想为他所创作的、往往遭到人们(包括一些严肃的专家们)非议的教堂音乐作一说明。人们一再说他的教堂音乐太世俗化、太歌剧化了,这隐约指出,他在迎合当时流行的一代世风。而真正的事实却是,他在此一领域的创作中并没有遵循那条著名的准则:音乐必须服从文字、诠释文字。难道这是唯一可能的音乐原则吗?众所周知,莫扎特即便在他的歌剧创作中也没有恪守那条原则。如果我没有听错,他谱写的音乐——不论是音乐还是其他方面的作品——都恰如其分而又自由地再现了预先为他规定的文字内容。音乐从文字获得主题、伴着它、烘托着它。音乐符合文字内涵——当然,这意味着:它与文字相对应而获得自己的生命。但是,在莫扎特音乐中,此一音乐配此一文字而不是任何其他文字,此一曲谱配此一篇章而不是任何其他篇章。他的音乐不可能是他安魂弥撒的音乐;反之亦然:他不可能使唱c小调弥撒曲中的《赞美您》或者《降生》的女高音与唱《费加罗》中《你们这些知人内心欲求的人》的侍童唱出同一个曲调,虽然他明显地赋予前者和后者同一种音色。他倾听文字,他尊重文字在此一处或彼一处所具有的特定内涵和品格,然后为此一处或彼一处的文字谱出音乐,不过,这是他自己的音乐——一种受文字约束而又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立构成体。至于他的音乐以这样一种处理方法是否与性文字相合,那么人们应该逐一进行个案分析(而不可先入为主地采用将音乐与世俗音乐区别开来的一般方法)。这样,人们当会愈来率深刻地——当然往往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以这种处理方法谱写的音乐恰恰符合文辞的客观内容。这也许是因为他的音乐也是从这样一个所在听知而又再现出来的,从此一所在虽然不可能将上帝与世界合为一体,然而与世界(彼此既不可混淆,也不可交换)之间的纯然相对的差别、它们最终的同属性质却是可以认识并且已经认识到了的:两者都从上帝而来,两者都向上帝而去。
最后,还有一个令人一想到便不胜伤心的问题:如果考虑到莫扎特短短的创作时间,人们便会发现,他留给我们的作品数量是惊人的。但是,他没有为我们留下来,而且我们永远无从知道的作品的数量更加惊人;因为在他生命的各个时期他都偏爱即兴创作,这就是说,在钢琴上自由虚构随意演奏:在公开的音乐会上也罢,或者更常常是面对几个听众连续演奏数小时之久。而此时所创作的东西事后并没有记录下来——这是整整一个曾经发出一次美妙音响然而却永远消失了的莫扎特音乐世界。
莫扎特的相貌如何?当然不像大多数保存下来的他的画像上的样子(它们全都将他画得有点像所谓的太阳神!)。他的连襟约瑟夫·朗格1782年绘的那幅(末完成)油画也许从神态到相貌都接近他本人。他有一对蓝色的眸子,一个尖尖的稍长的鼻子,是(据另一位英国人的描述)“一个显然很矮小的人,身材瘦削,面色苍白,有一头他似乎为之感到自豪的浓密金发”。此外,他喜欢打弹子、跳舞、饮番趣酒,“我曾见过他一次喝很多这种饮料”。这肯定不是一位立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的身分和职业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当他坐在钢琴前面时,他方才为人所注意(也许只有这时他的声音方才有人倾听)。这时他方才成为伟大的莫扎特。让我们感谢他,他至少在后来一再被演奏的乐曲之强有力的余音中使我们能够接近他。
——摘自卡尔·巴特、汉斯·昆著,朱雁冰、李承言译 《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
第20页
这个人极富有创造性,哪怕是在他模仿别人,或者说恰恰表现在他模仿别人的时候,事实上,他从来也不曾一味地模仿过别人。他在当时的艺术法则的框架之内从一开始便自由驰骋,而在后来则愈来愈自由。但是他并没有违背艺术法则,他不曾冲破这些法则,他在探求着,他的伟大恰恰在于在法则的约束下成为他自己。
在他嬉戏的背后是艰辛和勤奋。
他的使命便是使自己完全摆脱掉他的重大和细微的生活经验,一次再一次地帮助他生活于其中的音响宇宙中的一小块变成形体。这是,所产生的一切无一例外地都是,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向听众发出邀请,呼唤他哪怕是稍稍爬出他们那个本己主观世界的蜗居。
莫扎特的眼睛所视、耳朵所听、内心所想的是上帝、世界、人、他自己、天与地、生,尤其是死,所以,他是一个内心深处不断思忖的人,因而是一个自由的人。
莫扎特音乐是无比自由的,它摆脱了一切夸张、一切原则上的突变和对立。阳光照耀着,但不刺目、不消蚀人,不灸伤人;天穹披覆着大地,但却不给它以重负、不挤压它、不吞噬它。
第40页
“既然死——仔细看来——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终极目的,几年以来,我便与人的这位真正最好的朋友相识了,所以,它的形象对我而言不再仅仅是某种令人惊恐的东西,而是颇为令人感到安宁和宽慰的东西!我感激我的上帝,他使我有幸为自己创造机会认识死,将它看成是达到我们真正幸福之境的锁钥。”
“为了这一幸福感,我永远感激我的创造者并由衷地祝愿我周围的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幸福感。”
第9页
他之“独一无二”是否恰恰在于它不可能、也不想成为革新者、革命者,不可能、也不愿意有任何特别之处,他只能、也希望在他那个时代的音乐长河之中并依靠这条长河而生活和创作?是否恰恰在于他只能、也希望将音乐当作他独有的本己之物而使之发出声响?他之“独一无二”是否恰恰在于他只能、也希望作为学生——正式因此而“无可比拟”地成为大师?
这便是他的音乐所固有的激动人而又安抚人的性质。它显然是来自这样一个高层面,从此一高层而上(人们在那里将认知一切!)同时观察到了此在的右侧与左侧,即欢乐与悲痛、善与恶、生与死的现实及其局限。
人们百听不厌的不正是莫扎特乐队中那发生着、躁动着和激动着的东西?不正是那种种出人意料而又正当其时出现并以其特殊的高低音和音色而达到完美境界的东西?这一切不正是整个宇宙以缩微形式被表现于音响之中?显然,作为人的莫扎特听见了宇宙之音并使它——他自身只起媒介作用——歌唱起来。
莫扎特并不想说什么,他只是歌唱,只是传出声音。因此,他并不强加给听众什么,也不要求他们作出决断或者表明态度,而是让他们感到自由。
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件乐器,他只是让人去谛听他显然听见的东西,那是来自上帝造物浸润着他、在他心灵中升华,而现在又从他心灵中逸出的东西。
第5页
我所要感谢您的,简言之就是我发现不论何时听您的音乐,我都被置于一个美好而有秩序的世界的门槛之前,这个世界不论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雷雨交加之时,不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保持其美好和秩序,而我作为20世纪的人,每次都从中获得勇气,获得速度,获得纯洁,获得安谧。有您的音乐的辩证法萦绕耳际,人们既可以使青春永驻,也能够让憩境到来;既可以工作也能够休息;既可以得到快乐也能够宣泄悲伤。一言以蔽之:人们能够生活。
波兰古典音乐动画《土耳其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