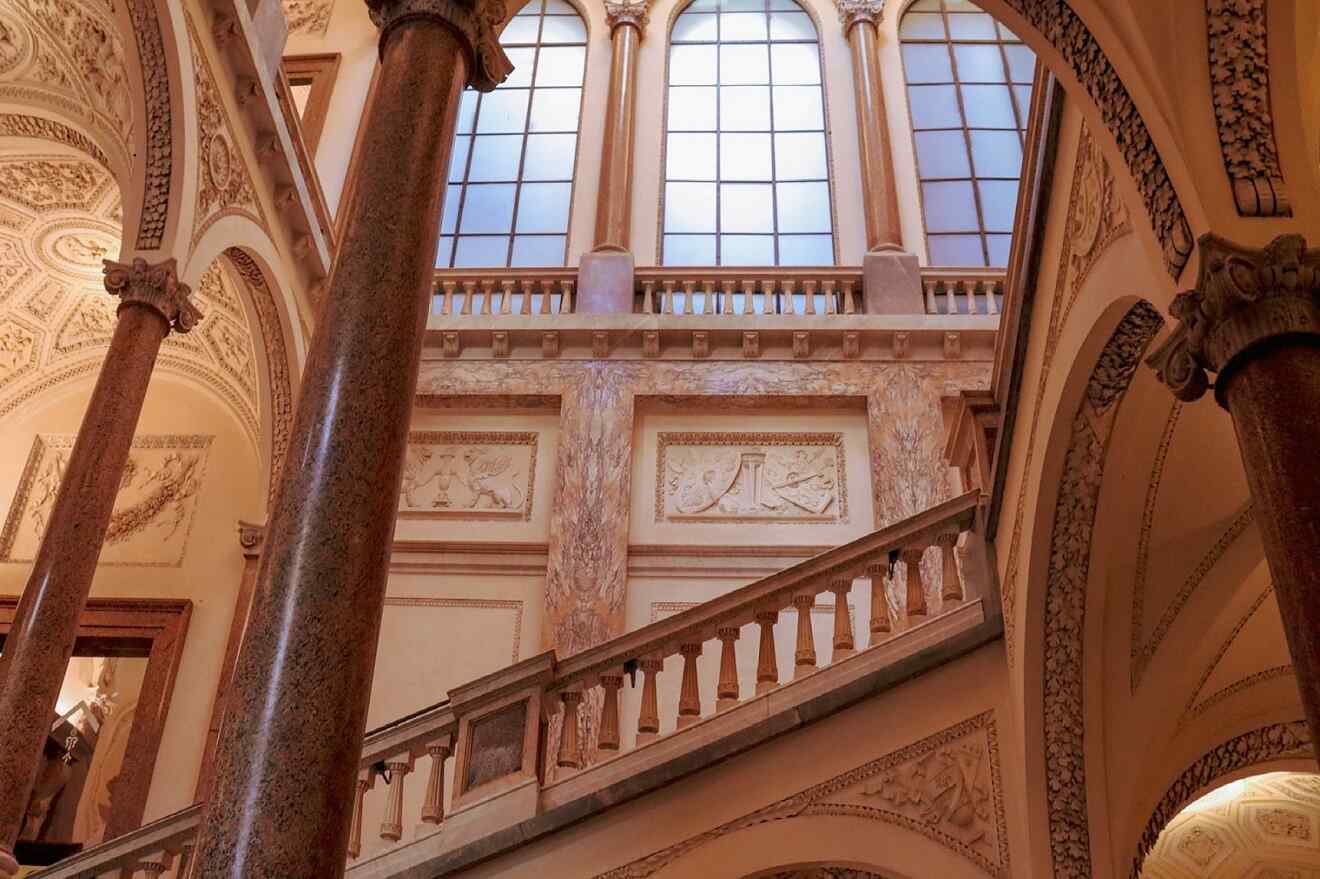?与重负嬉戏?
TheRunningCain
在高庭之上舞蹈,在众神面前祷告
爱因斯坦说,死亡就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了。伟大的心灵果然都是相通的。作为维也纳古典乐派三巨头之一,莫扎特的音乐的确能使浩瀚之星辰羞涩,使寰宇之天籁无声。而那包含在古典之中的强健的魂魄,在给予人们乐观向上的进取之心的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普遍的追求和期望。然而伟大的莫扎特却过得并不如意。大量的怨恨与嫉妒,以及更大的敌视,混合成一杯鸩酒,送到他的唇边让他喝下。在彼得·谢弗的剧本《上帝的宠儿》(Amadeus, 1979)里,我们看到在这场天才和庸才的世纪之战中,“上帝的宠儿”是如何败下阵来的:
死亡证明书上说他死于肾脏功能衰竭,加上长期的挨冻。
慷慨的赋格爵士掏钱给他办了个乞丐的葬礼,跟二十个其他的穷鬼一道扔进了没有标志的石灰坑里。
……
我当时觉得怎么样?当然是放心了!这我承认,
同时,也有对这个我参与毁灭了的人的怜悯……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教堂祈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成名吗?……
那好吧,我现在有名了!……
可是叫我出名的那些作品我自己清楚,毫无价值!……
而到了最后,上帝还留了最狠的一手!
他等到我淹没在名里,等到我对名都恶心了——
突然,我的名消失了。一点不剩!
……
那个高不可攀、麻木不仁的上帝的冷嘲热讽……
“萨列瑞,保护一切庸才的圣人!”(329-341)
,在对上帝的无休止的质问中完成了他伟大的复仇计划。这由嫉妒而渗出的毒液早已将他深深腐蚀,纵使冒着遗臭万年的风险他也要遵从欲望的驱使,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然而只有在死亡里才能生出不朽,永生神的圣殿和宝座也是从十字架和坟墓中升起的。换句话说,胜利来自于失败,处境越是黑暗,神的脸才越是光明。所以海明威那本短篇小说集叫做Winner Take Nothing(1933),而格雷厄姆·格林有一个与之颇为相对的中篇小说,叫做Loser Takes All(1955),作者意图已经很是明显。而萨列瑞显然不这么想,他既想要天国的荣耀,又想要世俗的名望。不得不说,他在这个剧本中恶事做尽,却像个悲剧英雄,让人怎么也恨不起来。
然而这段谋杀的故事其实是经不起历史考证的。萨列瑞与莫扎特的确是竞争对手,但莫扎特之死可以说与萨列瑞毫无关系。但凡对野史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莫扎特的一生是重口味+三俗的一生,他对粪便的疯狂崇拜和在得知自己得了以后的疯狂与欣喜让他只活了35岁,这和萨列瑞能有什么关系呢?况且莫扎特死后,其子也是在萨列瑞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音乐学习的。这样高姿态的敌手,值得拥有。
可惜,不管萨列瑞是恶棍还是英雄,他最终还是淹没在无垠的大海之中了。莫扎特却一下越出了古典乐派的范畴,被后世的浪漫主义者不断挪用和崇拜。
譬如克尔凯郭尔就在《非此即彼》(Either/Or)中专辟章节讨论对莫扎特的爱(虽然他只爱《唐璜》里的莫扎特):
Immortal Mozart! You to whom I owe everything— to whom I owe that I lost my mind, that my soul was astounded, that I was terrified at the core of my being—you to whom I owe that I did not go through life without encountering something that could shake me, you whom I thank because I did not die without having loved, even though my love was unhappy. No wonder, then, that I am much more zealous for his glorification than for the happiest moment of my own life, much more zealous for his immortality than for my own existence. Indeed, if he were taken away, if his name were blotted out, that would demolish the one pillar that until now has prevented everything from collapsing for me into a boundless chaos, into a dreadful nothing.
不朽的莫扎特!我把一切都归之于你——把我丧失了思想、我的灵魂受到震撼、我存在的核心受到恐吓都归之于你——我把要是没有遇上某种可以震撼我的东西就不能经历生活归之于你。我感谢你,因为如果没有爱过,即使我的爱情是不幸的,我也不会死去。因而,不足为怪的是,我对于颂扬他比对于我自己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要有热情得多,对于他的不朽比对我自己的存在要热情得多。真的,倘若他被夺走,倘若他的名字被抹掉,那么这将毁掉一根支柱,这支柱到现在对我来说尚未使一切化为无边的混乱,尚未使一切化为可怕的虚无。(《或此或彼》,2007:60)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正在欧洲大地上蔓延。精英们在各国涌现出来:在德国有施莱格尔、席勒、海涅、荷尔德林,在英国有华兹华斯、济慈、拜伦、雪莱,在法国有德拉克罗瓦、席里柯,在克尔凯郭尔的祖国丹麦则有厄楞士雷革、海贝尔、古隆维格、托尔瓦德森等人。这场狂风暴雨般的思想浪潮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理想,而且也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呼唤。更进一步说,浪漫主义始终是文学、艺术乃至人生哲学的基质,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青年时代的克尔凯郭尔亲历了这场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并且从中汲取了养料。应当说,他的诗人气质,以及他对存在问题的关注,都与浪漫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贵为存在主义之父,其一生也是致力于对浪漫主义进行深度挖掘。按照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的说法,存在主义无非就是浪漫主义在当代的一种极端延续罢了。而作为古典音乐流派的扛把子,莫扎特却是深受浪漫主义者喜爱,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莫扎特的天赋正好契合了浪漫主义者对独创性天才的呼唤,另一方面则在于,他音乐中的那份纯净的欢快部分地中和了浪漫主义者的天性的忧郁,使他们在拼命逃向无限的自我和想象的王国的同时,至少能保持一种与现实的微弱的联结。因此,纵使克尔凯郭尔将莫扎特放在了人生道路诸阶段上最低的那个位置(审美阶段,也即大多数人所处的阶段),他还是没有完全跳入自我的陷阱,而是用古典音乐的精神来引领自己上升。他知道自己的一生注定是诗性的,但他同样渴望莫扎特的德性。
但或许并非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想要回到现实理性中去,比如说尼采。他比克尔凯郭尔晚生了几十年,似乎也并没有读过克氏的著作(可能与当时的翻译速度有关吧,而且用丹麦语写作的克氏在欧洲大陆实在是很边缘的存在,勃兰兑斯就曾在《世界文学》一文中为克尔凯郭尔鸣不平,称其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欧洲大陆却无人知晓”),所以他并未在神-人关系中寻找人生的意义,而是遵从于强力意志。他的梦想是无限的上升,是在经历过上百个灵魂、上百个摇篮和分娩的阵痛之后,成为真正的超人(Übermensch)。而莫扎特显然是无法助他完成这一超人梦的。所以,我们在克尔凯郭尔到尼采的这一转换中,看到的是浪漫主义的精进,以及从莫扎特精神到瓦格纳精神的突变。
流 浪 的 该 隐
TheRunningC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