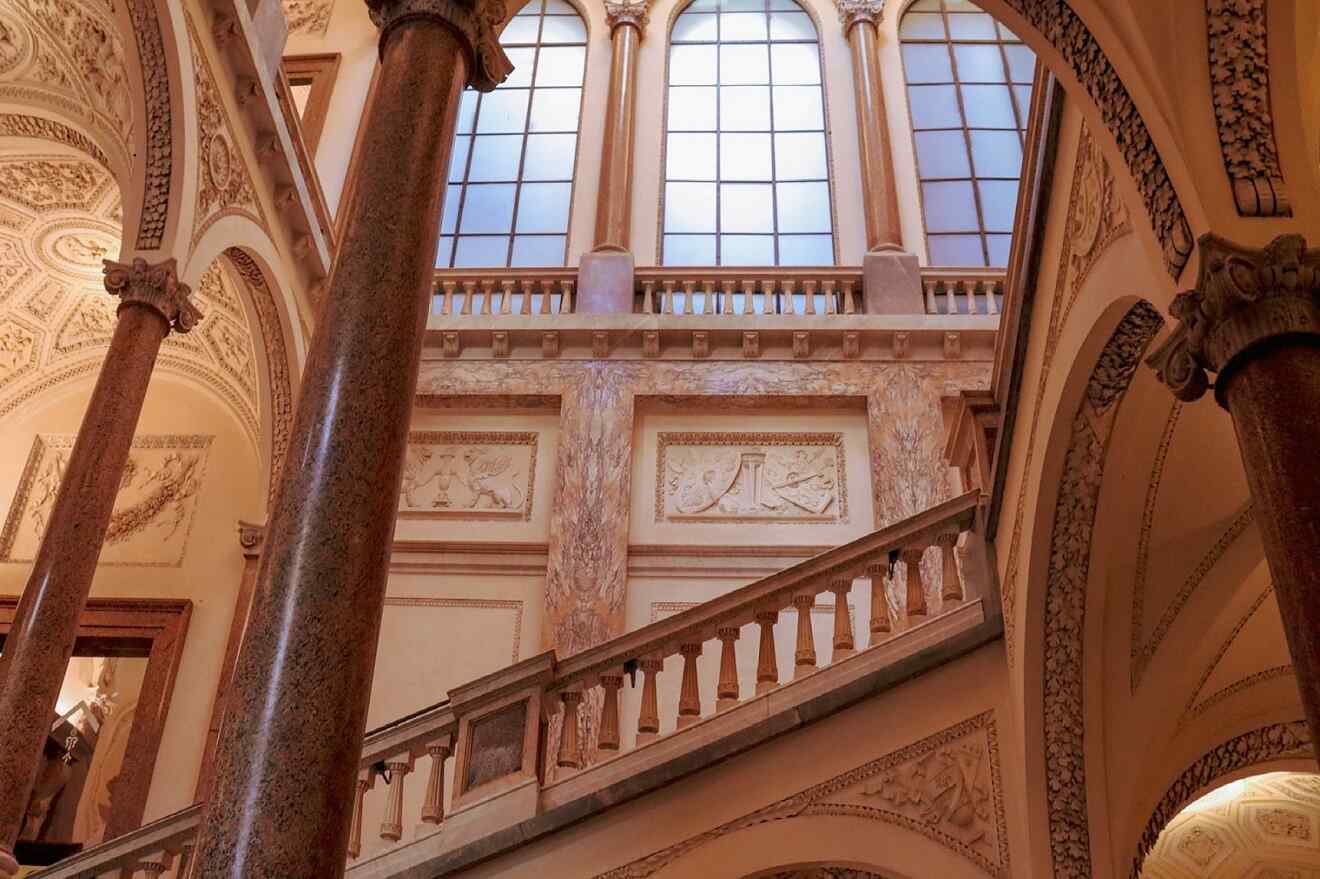2018年第3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图绘他者——
19世纪东方题材绘画中的
种族、
金松林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1
摘要
19世纪伴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东方题材的绘画悄然盛行,艺术家们不仅关注异域的风俗风景,而且将画笔延伸到浴室、闺房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后宫。由于受殖民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影响,他们对东方并非客观再现而是任意想象和歪曲。东方在他们笔下被塑造为欲望的天堂,女性特别是黑人妇女备受歧视,。
关键词
他者;女性;想象;种族;性别;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英、法、荷、葡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将目光转向东方,并且利用坚船利炮进行疯狂的殖民扩张,这一过程于19世纪抵达高潮。据历史记载,他们以年均8.3万平方英里的速度推进,到1878年已占领了全球约67%的土地,从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到中东的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等均沦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当欧洲列强的瓜分尚未完结,他们还在为争夺更多的殖民地而相互斗争时,克尔南(V. G. Kiernan)说所有的帝国又努力巩固地盘、调查了解、深入研究,当然还要用他们的管辖权来控制各自所占领的疆土。
,他们还利用更加隐蔽、更显温情脉脉、更具有欺骗性的文化手段。一些来自帝国的学者、旅行者、思想家、理论家、小说家、艺术家和诗人为殖民地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巴特·摩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等在他们的后殖民理论著作中列举了许多名字,如雨果、司各特、拉马丁、热拉尔·德·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阿尔弗莱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分析,揭开了那些游记、小说、随笔中隐藏的殖民策略。“可以很有把握地说,19世纪的殖民话语中极少有文字不带着种族语汇和种族观念的印记”,“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
博埃默和萨义德的上述观点的确非常深刻,然而其涉及的领域毕竟有限,特别是他们从未将19世纪西方画家关于东方题材的绘画纳入理论研究的范围。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在他的小说《坦克雷德或新》中曾说,东方其实也是一些艺术家的“谋生之道”。如安格尔、雷诺阿、德拉克洛瓦、皮埃尔·路易·布沙尔(Pierre-Louis Bouchard)、让-莱昂·热罗姆(Jean-Leon Gerome)、弗朗西斯科·保罗·米切蒂(Francesco Paolo Michetti)、约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John Frederick Lewis)、爱德华·德巴-蓬桑(Edouard Debat-Ponsan)、乌里奥·罗萨蒂(Giulio Rosati)、莫里茨·斯蒂夫特(Moritz Stifter)等创作了大量东方题材的绘画。
就内容而言,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自然风景,优美的尼罗河、广袤的阿拉伯沙漠、小亚细亚的自然山川都是他们描摹的对象;二是社会风俗,如的婚礼、宗教仪式、休闲娱乐、商贾集市、节日的盛况等;三是女性题材的绘画,其中既包括普通女性的家居生活,也包括奥斯曼帝国后宫中的宠妃和女奴的生活。从数量上说,风景题材的绘画并不多,有名的就更少,而风俗画和女性题材的绘画占了绝大部分,由此可以推断,这些殖民主义时代的画家重点关注的并不是东方的山川景物,而是东方的风土人情以及由它们所展现的差异性——更确切说,是异国情调,这些事物不仅符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而且迎合了他们对东方的想象。因此,对风俗画和女性题材的绘画的分析便成为本文的重中之重。
01
跨文化视野中的他者形象
法国著名的比较学者路易·马西尼翁(Louis Massignon)说:“为了理解他者,不应将对方当作自己的附属品,而应成为对方的客人。”这是他积极倡导的跨文化沟通的策略。“成为对方的客人”,也就是要和对方平等相待,充分尊重和理解对方,而不是将自己的情感好恶或者偏见置于他者之上,更不能将对方视为自己的敌人或奴仆,用讥讽甚至贬斥的态度来描述他者。马西尼翁的主张无疑是跨文化沟通的理想状态,事实上,这种状态很难达成,或者根本就无法达成。在与他者沟通的过程中,任何个体都摆脱不了自身的民族身份、文化观念以及长期积淀下来的历史意识,这些东西总会或明或暗地影响双方的交流。,欧洲人对东方的观念就彻底改变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以一种崇敬和恐惧的心理来面对东方,而是一种倨傲的姿态来审视东方,正如拉斐尔·丢·芒斯(Raphael du Mans)在他的地理学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欧洲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东方正被西方的科学技术所超越而落伍。面对繁华不再的旧世界,来自新世界的欧洲人怎么会产生艳羡呢?在19世纪东方题材的风俗画中,画家们的殖民心态昭然若揭,他们凝视东方,描述东方,替东方说话,目的并不是为了呈现东方的本来面目,而是矮化它,歪曲它,使之和欧洲人的想象契合。所以,后殖民理论家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er)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说:“东方主义者的东方是一个构建的赝品,通过东方,西方解释、说明、论证了其自身的时代关注,并使之具体化。”如果说东方是一块填了色的画布,那么这块画布所映现的并非真正的东方,而是欧洲人自己的面孔。
德拉克洛瓦是法国画坛著名的浪漫主义旗手。他在造访东方之前,。该作取材于当时希腊人为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而进行的一场“独立战争”中的情景。画面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前景中,惨遭蹂躏的平民、被劫掠的少女、正在寻找母乳的幼儿和飞扬跋扈的土耳其士兵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手握钢枪,骑着高头大马;远处家园破碎,哀号遍地,烟尘滚滚。:“他(指德拉克洛瓦——引者加)的作品都是破坏、、大火,都是为反对人的永恒的、不可救药的野蛮而作证:被焚的、冒着烟的城市,被扼死的人,被的女人,被扔在马蹄之下或者发疯的母亲的匕首之下的儿童。我认为,整个作品就像是为宿命和不可平复的痛苦而写的一曲可怕的颂歌。”它通过强烈的对比表达了画家对希腊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土耳其人的憎恶。在德拉克洛瓦的笔下,东方民族意味着专制、残暴和野蛮。不久,他创作的《沙尔丹纳帕勒之死》(1827)进一步印证了这点。
图1 ,1824
1832年,德拉克洛瓦以随员身份陪同法国驻苏丹大使莫内伯爵到访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这次北非之行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迅速摆脱了对历史和神话题材的迷恋,继而将目光转向了真实可见的生活。《卖水果的阿拉伯小贩》《在马厩中打斗的阿拉伯马》《穿着带有包头巾条纹呢斗篷的阿拉伯人》《坐着的摩尔人》《摩洛哥女人》《犹太新娘》《乡间的阿拉伯人》《摩洛哥的苏丹和他的随从》《丹吉尔的狂热教徒》等都是这次北非之行的成果,它们有些是在旅行途中就已完成的,有些是在归国后加工而成的,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东方风情。“在许多方面,他们要比我们更加顺乎自然,比如说,他们的衣裳,他们鞋子的形状,等等。因此,他们所做的每样东西里面都有美。可我们呢,妇女穿的胸衣、狭小的鞋子、套管式的衣服,这些全都是可悲的东西。我们得到了科学,却牺牲了优美的风尚。”德拉克洛瓦在日记中不时流露出对东方的欣赏,可是一旦落实到画布上却全然是两样,或者说,先前那种殖民主义的态度又死灰复燃。在他笔下,东方不仅贫穷落后,而且是好征服的。《丹吉尔的狂热教徒》(图2)就是这种心理的集中体现——当象征西方文明的神父率领他的随从来到丹吉尔,立即受到城中贵族和普通民众的欢呼。,那个穿白色衬衣的男子行为乖张,然而在他身边,有人已经晕厥,可人们依然架着他继续奔跑。通过这样的场面,德拉克洛瓦无非是想粉饰历史、美化现实,即西方人来到东方是为了传播福音,这一神圣的工作非但没有遭到当地民众的反抗,反而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这显然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其最典型的特征就在于赤裸裸地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论,并以此为基础,对他者进行操控。所以,德拉克洛瓦有关东方题材的绘画是殖民主义的缩影,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殖民者的心性。
图2 《丹吉尔的狂热教徒》,1837—1838
19世纪,像德拉克洛瓦一样游历东方的欧洲画家还有约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弗雷德里克·阿瑟·布里奇曼、乌里奥·罗萨蒂等,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风情。在他们笔下,东方和东方人都被符号化了,换言之,他们是以一种符号化的方式来图解东方。形式各异的伊斯兰建筑、阿拉伯长袍、波斯地毯、包头巾、香炉、瓷器、兽皮、羽扇、丝绸、水烟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层出不穷,它们既建构出一种真实的生活场景,同时又营造出十分浓郁的东方情调。刘易斯曾在开罗生活过长达十年之久,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说:“我具体画了什么并不重要,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你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竟看到了什么。我尝试通过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向你们呈现我所看到的东方世界,其中虽然不乏想象的成分,但我希望它们能够给大家带来愉悦。至于东方究竟怎样,我觉得不值一提,因为它们根本就无法和欧洲相比。”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画家之代表,刘易斯的这番话彻底道出了他们的方法和用意:东方之于西方,其价值就在于可利用性。为了达到愉悦的目的,可以任意地歪曲它,即便是添油加醋。安格尔、莫里茨·斯蒂夫特、弗朗西斯科·保罗·米切蒂等从未涉足东方,不也照样创作了大量东方题材的绘画吗?因此,萨义德评论说:“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达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而这些表述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对于以上所提到的画家来说,他们只要掌握了这些代码,自然就可以制造出东方形象。
实际上,异国情调是差异性的代名词,其本质就在于对象的不可穿透性。如果主体可以轻易地穿透他者,那么就没有任何差异性和神秘性可言。相反,正是因为对象的不可穿透,所以才会激发主体的欲望。在《从巴黎到》一书开篇,夏多布里昂就直言不讳地说:“一次东方之旅可以完整地实现我长期以来决心完成的研究工作;我充分地领略到了美洲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的大自然的遗迹,但我对于人类辉煌文明却不甚了解,知道的只是克尔特文化和罗马文化。我还要去雅典、孟斐斯、迦太基,参观那里的文化遗产,当然,我也不会错过的风采。”我们随后看到,夏多布里昂对东方的表述始终充满了自我中心论的色彩,其文字不过是旷日持久的欧洲经验的再现而已。他口口声声说“不会错过的风采”,可他实际上见到的不过是罗杰·本雅明(Roger Benjamin)意义上的“海市蜃楼”。包括画家在内,“尽管他们试图真实再现眼前之景,不论他们采用何种专业技法,总难免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去理解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的海市蜃楼是指任何艺术家不可能获得对异域文明的客观认识”。所以,当他们信心百倍地将东方展现在画布上,但它不是被扭曲就是趋向消亡。总而言之,东方总是被一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
02
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描绘
,也可能来自于文化,,但它的力量却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无法忽略它的存在,那就是欧洲白种男人对于东方的性幻想。在西方,由于传统根深蒂固,人们内心的欲念总是遭到压抑。认为性是专门为婚姻而设的,它视婚姻之外的一切性行为均为犯罪,甚至包括各种淫念,“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福柯在《性经验史》开篇追溯,在17世纪初叶及之前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举止袒露,言而无羞,对性生活比较坦诚,无需太多的顾虑。然而,在这个“人成长的时代”之后,黄昏迅速降临,“性经验被小心翼翼地贴上封条。……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对于性,人们一般都保持缄默,惟独有生育力的合法夫妇才是立法者。……一切没有被纳入生育和繁衍活动的性活动都是毫无立足之地的”。人们制定了一系列的道德、法令和禁忌,对婚姻之外的性行为进行围追堵截。所以,从18到19世纪,,还是被谴责和惩罚的对象。那么,如何释放自己内心不歇的欲望,许多欧洲白种男人将目光纷纷转向了东方,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竟然将自己对于东方的欲望要求同西方控制东方的集体目标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1850年,福楼拜沿尼罗河而上游览了埃及首都开罗。他在那里遇上了当地有名的舞女库楚克·哈内姆(Kuchuk Hanem),并且在欣赏完她的蜂舞之后就兴奋地和她上了床。她感觉细腻,风情万种,令福楼拜如痴如醉。他在日记中说:“那一夜是漫长的、极度强烈的狂欢——我留下来就为这个”,“分手的时候,我们却有春宵苦短的惆怅,从我们的拥抱中流露出悲伤和爱”。库楚克的麻木和放荡激发了福楼拜的无尽遐想,当然也影响到他的创作,在小说《圣安东尼的诱惑》《萨朗波》《情感教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舞女库楚克的影子。“东方女人不过是一部机器,她可以跟一个又一个男人上床,不加选择。”这种论调既非自福楼拜开始,自然也不会到他结束。在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爱德华·威廉·雷恩(Edward William Lane)、阿尔封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杰拉·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等人的作品中,也充斥着此类论调。东方女性通常被塑造为体格妖艳且生性放荡的形象,作为一种集体的想象物,这些作品或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同时代画家的创作,使他们对于东方女性的呈现完全偏离了现实,而肆意歪曲和羞辱。当然,她们的存在是必要的,无论是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性对象。钱拉德·塔尔佩德·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曾说“妇女是男性施暴的牺牲品”,我们也可以说“东方女性是欧洲男人施暴和施淫的牺牲品”,在整个19世纪,他们对东方女性的“侵犯”从未停止过。
让-莱昂·热罗姆有两幅名作:一是《奴隶市场》(图3),一是《土耳其奴隶市场》(图4)。从建筑物和人物服饰可以判断,作品描述的是东方场景。在第一幅画中,买主们让女奴在大庭广众之下脱掉衣服,一丝不挂地裸露在他们面前,为了检查她的牙齿,他们还粗鲁地将手指塞进她的嘴巴……整个过程就像买头牲口一样。第二幅画告诉我们:这些奴隶(性或性对象)俯拾即是。卖主趾高气扬地坐在店铺里,贩卖她们就像贩卖某个普通的物件。为了兜售她们,甚至要求她们脱光衣物,有时连哺乳期的妇女都不放过。就取材而言,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对东方的丑化,还是对东方的奇观化。其中,既反映出画家本人及其观看者的欲望,也折射出他们的殖民心态。欧洲历史悠久的父权制文化、种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这些作品中神奇地组合在一起。凭借它们,或者说,借助于那种混杂性的艺术手法,东方女性(经常被简化为性)像大众文化中其他类型的商品一样被标准化了,其结果是画家和观看者不必前往东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它,若是他们想得到的话。
图3 《奴隶市场》,1866
图4 《土耳其奴隶市场》
安格尔的创作就是典型的例子。1863年,他完成了后期的经典之作《土耳其浴室》(图5)。“这幅作品只是中等尺寸,集合了20多个形象,以各种你所能想象得到的姿态沉浸在东方情调浴室的欢愉中。她们演奏乐器、舞蹈、听音乐、吃东西、喷香自己的头发,身边有提供饮料的侍女。总之,她们在一个放松的情绪下休息,偶尔拥抱彼此,画家以一种静物画的方式对这些形象进行安排处理。”不能忽略的是这幅画完全出自于画家的想象,因为安格尔从未涉足东方,他对东方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同时期的画家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但它竟然如此逼真。在构图上,画面呈圆形,这显然是一个经过巧妙设计的窥视的场景。谁在窥视?在那些来历不明的人中,至少有一人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画家本人。不过,安格尔在这幅作品中投射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欲望,还包括其他人的欲望,特别是那些欧洲异性恋男子的欲望。通过窥视这种违禁行为,他们能够获得非常强烈的观看体验。乔治·巴塔耶说:“任何人,无论是谁,都无法怀疑色情带给我们的极端的、过度的、心荡神驰的特征。”在19世纪,类似作品还有很多,如爱德华·德巴-蓬桑的《按摩》、让-莱昂·热罗姆的《浴室》《土耳其浴》《布尔萨的豪华沐浴》、保罗·路易·布沙尔的《沐浴之后》。西尔韦尔·洛特兰热在为让·波德里亚的著作撰写的引言中强调,艺术是“串通的艺术”。这种“串通”不是某些人的私下行为,而是源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对于殖民主义时代的画家而言,他们在将东方女性化了的同时,也将女性东方化了。在他们的作品中,东方/女性既是被表述的对象,也是被窥视和施淫的对象。
图5 《土耳其浴室》,1863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空间越是私密,它所激发的欲望会更加强烈。“因为在象征范畴内,位居首位的应该是诱惑,而性只是一个额外之物。”波德里亚认为人和动物之所以不同,主要就在于他们所迷恋的其实是不可能或不可得到之物。而用拉康的话说,欲望的本质即匮乏,正因为其“无”所以它才会唤起人们源源不断的欲望。如果说土耳其浴室还是一个相对公共的空间,那么帝国的后宫就迥然不同,那是一个绝对私密的空间,除了苏丹及其家人以及被阉割的太监和宫女外,任何人都不准随意出入,否则会遭受十分严酷的惩罚。在后宫,嫔妃和宫女无数,但大多数女人很少有机会和苏丹同床共枕,她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独守空房,无聊度日。因此,英国历史学家杰森·古德温(Jason Goodwin)将这一被权力禁锢的空间形容为“后宫囚笼”。从塞尔柱时代开始直到19世纪,很少有欧洲学者、旅行家、作家或艺术家被获准进入帝国的后宫,所以他们对于这一空间充满了遐想,莫扎特的著名歌剧《后宫诱逃》、伏尔泰的《老实人》、英国著名的《淫荡的土耳其人》就是典型的例子。让-莱昂·热罗姆、弗里德里克·阿瑟·布里奇曼、莫里茨·斯蒂夫特、皮埃尔-路易·布沙尔等艺术家也创作了大量后宫题材的画作,这些作品主要表现苏丹寻欢作乐和宫女们梳妆打扮、休闲娱乐、更衣沐浴等情景,画面多具有挑逗性,如弗朗西斯科·保罗·米切蒂的Odalisque。该画最显眼的部分自然是宫女形象,她赤裸着上身,趴伏在软榻上,血色鲜艳,肌肤白皙,坚挺,臀部和背形成优美的曲线,在百无聊赖中等待苏丹的宠幸。吉拉德-乔治·勒迈尔(Gérard-Georges Lemaire)在评价该画时说:“它作为一个缩影,集中反映了西方对后宫的想象,其中既体现了男性的欲望,也包括帝国的欲望。。”
图6 Odalisque
如许众多的画作基本模式化了,用萨义德的话说,它们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认识东方,而是塑造、重建以便最终控制东方。“我们没有必要寻找描述东方的语言与东方本身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因为这一语言不准确,而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想做到准确。它想做的只是,正如但丁在《地狱篇》中所做的那样,在描写东方的相异性的同时,图式化地将其纳入一个戏剧舞台之中,这一舞台的观众、经营者和演员都是面向欧洲的,而且只面向欧洲。”为了欧洲人的利益,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将东方制造为欲望的天堂。
03
处于屈从地位的黑人妇女
在这些画布上,还有一类形象引人深思,那就是不断被表述却又始终沉默的黑人妇女。她们的形象既出现在日常生活题材的绘画中,也出现在后宫题材的绘画中,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她们的存在,这一选择性的遗忘或忽略本身就已体现出她们卑微的种族和性别地位。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小说《她们眼望上苍》中有个细节:“那白人把包袱扔下,叫那黑人捡起来,因为他必须这样做,但是他并不背着它走,而是递给了家里的女人。按我的理解,那个黑女人就是这个世界的驴子。”这一细节生动形象地反映出黑人妇女的地位:她们既受到白人的压迫,同时也受到黑人男性的压迫。在由西蒙德·波伏娃所建构的性别阶梯中,她们永远处在最底层,在那本所谓的“女性”(《第二性》)中,她们甚至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由白人建构的历史中,她们所拥有的身份就是奴隶,就是“驴子”,就是“狗”,就是她们本应该是而不是的“人”。“我所做的只是工作,像狗一样工作!从早干到晚。我没有幸福,从来都没有。”这既是贝西——非裔美国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小说《土生子》中的一名黑人妇女——对自己命运的总结,也是声嘶力竭的呐喊。但是,在19世纪的殖民主义制度下她们谁也逃脱不了遭受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厄运。
白种的欧洲人始终相信他们是出类拔萃的,他们不仅具有冒险精神,还具有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当这些优点累加在一起,使他们确信自己比其他民族更适合于管理这个世界。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威廉·罗伯逊·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安德鲁·兰(Andrew Lang)等早期人类学家曾明目张胆地为这一谬论提供佐证。吉卜林、康拉德、威廉·阿诺德(William Arnold)、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等同时代的小说家也位列其中,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将殖民地的原住民特别是黑人描写成低等的、懦弱的、愚蠢的,这类描写提供了认识的或意识形态的暴力,起到了为更加赤裸裸的占领助威呐喊的作用。在殖民小说中,他们也塑造了一些黑人女性形象,如《她》中的乌斯塔尼、《基姆》中沙姆里的“女主人”、《黑暗之心》中库尔兹的非洲情妇,她们——更确切地说,她们黑色的身体——虽然具有诱惑力,但是与浪漫的爱情无关,不过是白人英雄归来后所得到的奖赏或者一次偶然的性放纵而已。作家的批判和主人公的忏悔不仅能增强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种族与性别歧视,而且有助于维护这种偏见,即白人男子与黑人女性的结合是一种堕落,而几乎所有细节都被情色化了。奴隶、保姆再加上荡妇,就是19世纪的欧洲文学公开塑造的黑人女性形象。著名的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在《黑人凝视:种族与表征》中说:“她们这些刻板的形象不仅符合殖民者的利益,而且符合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念,。”在绘画领域,艺术家们也秉承了时代主潮,他们对黑人女性的种族与性别歧视有增无减。
他们是怎样描述黑人女性形象的呢?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区分。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中曾说:“我们见不到存在于语言结构中的权势,因为我们忘记了整个语言结构是一种分类现象,而所有的分类都是压制性的:秩序既意味着分配又意味着威胁。”为了建立种族秩序,画家们将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彻底地区分开来,人为划定她们之间的界限——白人女性是主人,而黑人妇女是奴仆,她们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毫无平等可言,而是一个统治着另一个。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通过图像来确立种族之间的壁垒对于维系白种优越论至关重要。当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习惯成自然,就会为欧洲的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在这些作品中,区分既是普遍的语法,也是意识形态的修辞。具体而言,包括这些技法:一是在景别上进行区分。一般来说,画面前景更加惹人注目,而后景往往容易被忽略。所以,画家们在构图的过程中总是选择将重点表现对象放在前景的位置,而将其他的对象放在后景的位置,如安格尔的《土耳其宫女和女奴》(图7)。在前景的位置,是白种女人性感裸露的身体,她侧卧于床榻之上,姿态慵懒,雍容华贵。左边弹琴的女奴神情超然,仿佛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之中。而在她们身后,那位黑人妇女面目模糊,沉默肃立,其身份地位和白种女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二是在衣饰上进行区分。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Joanne Entwistle)认为,“衣着或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为了展现白人女性性感迷人的身体,画家们会让她们完全赤裸或者仅以轻纱掩体(通常是下半身),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安格尔的画作。波德里亚说:“女性的这个威力就是诱惑(séduction)的威力。”为了渲染这种气氛,画家们会尽情地赋魅。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黑人女性的身体非但不美,而且有碍观瞻,所以会让她们披挂整齐,将其“丑陋的身体”隐藏在宽大肥厚的衣服里。三是在技法上进行区分。他们会用十分细腻的笔法精心刻画白种女人,她们身体的轮廓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起伏变化,他们都会认真地对待。但是对于黑人妇女,他们却完全丧失了耐心或者觉得根本就没有细心描摹的必要,所以总是落笔草草,如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的《奥林匹亚》(图8),画中白女人的睡姿堪比乌尔比诺的维纳斯,而她身后的黑女人被处理的面目模糊,简直像个鬼魂。作为黑人妇女的杰出代表,贝尔·胡克斯批评说:“在一个系统性地对黑人女性进行贬损的文化中,只有处在为他人服务这个范围之内,我们的存在才被视为有意义。”所以在这些画作中,她们的形象都是为奴为仆,作为一种陪衬而存在。有些画家之所以在作品中留下她们的影子,主要是为了制造东方情调,其存在实与器物无异。由此可见,艺术作品并非纯而又纯的,。范迪安在《世界艺术史》的前言中说:“艺术作品在整体文化构筑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可能包含着该文化的宗教信仰,道德标准,美学观,也透露了社会阶层中的不同的等级、界限以及禁忌,并且发挥着维系使之不朽的功用。有些作品没有明显的说教成分,,其效果神不知鬼不觉。西方艺术中一直保持有古希腊的审美观而助长了种族偏见——在心智、品性或美丑方面的白种人优越主义。没有什么比西方艺术中的黑人形象更能看出视觉意象对文化结构的维系力了。”在殖民主义时代,这种状况体现得更加明显,也更加肆无忌惮。
图7 《土耳其宫女和女奴》,1842
图8 《奥林匹亚》,1863
04
结语
这些作品影响深远,它们不仅把东方变成一种模式化的知识生产,而且通过巧妙的文化手段将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合理化和合法化了。罗伯特·扬(Robert Young)在其著作《白色神话》中说:“作为殖民他者的效应,长期以来这种知识系统的运作不过是法农如下观察的一个倒置:‘欧洲不过只是第三世界的创造物。’”对于这些画家来说,他们的创作非但没有避开欧洲中心论的陷阱,反而越陷越深,结果导致其作品严重丧失了颠覆群体价值的功能,更不提人文主义精神。当然,对于它们,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因为这些作品毕竟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任何作家或艺术家对异国的感知总是离不开社会集体的意志和想象,建制的目光及其效果会自动地嵌入形象的修辞,并且留下踪迹。今天我们反思这些作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揭露有关事实,更是为了警醒人们应该牢记:“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解殖民化和去殖民化的过程依然艰难而漫长!
秉承以美育人理念,发扬艺术精神,倡导人文关怀
投稿邮箱:myxkzz@163.com
推送排版时可能存在部分删减,请以原刊论文为准
长按二维码或输入微信号"myxkzz"关注我们